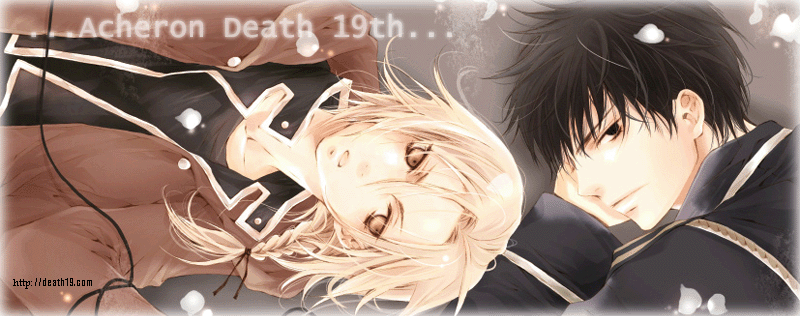番外燕详夜间飞行
三年后。
“你去过斯德哥尔摩吗?”隔壁座位是一个金发碧眼身材胖大的欧洲老太太,笑容慈祥和煦:“那是个很美的城市,我从小在那儿长大,噢,年轻人,你一定会喜欢那儿的,我保证。”
我微笑着跟她道谢,我当然会喜欢那儿,因为有人正在那里等我。
广播里反复播放着系好安全带的提示,我收起了简易桌,关掉头顶的照明灯,将座椅调到舒适的高度,侧头看着身边的舷窗。
飞机已经在滑动了,外面细细的雨滴斜斜划过玻璃,留下一道又一道透明的水渍,透过水渍看去,我所熟悉的城市渐渐变成了卫星地图般的格子图画,抽象极了。
闭上眼,我在脑海中勾画他的轮廓,如同沙画一般用记忆描绘我们从相识到分离的一个个场景,时间被定格成一个个AVI片段,幸福的愈幸福,酸楚的愈酸楚。
我第一次见到陈树,是在吉田会所的大堂里,那天下午我约了几个建筑商打麻将,送走他们后站在会所大堂里等老赵取车,这时旋转门动了,一个颀长挺拔的身影走了进来。
看到他的那一刻我有些轻微的惋惜,他长的真好,大约是会所里我见过的最上乘的货色,只是穿着太过穷酸朴素。
我想他应该还是个学生,搞不好还是个高中生。可惜,来这里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来消遣的,另一种是提供消遣的,他明显不属于前者。
他脸色不好,大概是嗑过药,现在的孩子真了不得,小小年纪就出来卖,还嗑药,比我年轻的时候是放得开的多了。
车子来了,我没有多想,推开门走了出去。
真没料到,不过七八个小时,我居然在小林的诊所里再次见到了他。
钱非的破坏力真他妈不是盖的,要不是那件破破烂烂的格子衬衫,我差点认不出他来。
他了无生气地躺在病床上,漂亮的脸上印着乌黑的指印,衬衫敞着怀,胸口腰腹全是伤痕,肋下有一块恐怖的凹陷,应该是骨折了。
我真是烦透了钱非那一套,搞同性恋就好好搞嘛,非喜欢玩儿SM,他就不能正常点儿吗?
后来,当我看到钱非带着脖套歪着脑袋跟郑元龙耍无赖的时候,差点没笑出声来。
原来不是那么回事,有意思。
我翻看了他的学生证,陈树,好名字。
以前弟兄们一起在会所里玩儿的时候,我也跟风弄过男孩,但仅限于娇小妩媚的类型,用嘴的,说实在的跟弄女孩没什么区别。
所以我从来不怀疑我的性向,只是大概这两年年纪大了,人也比较稳重,对那种事儿不太热衷了,有时候半个月一个月的忙生意,都没想起过找个人打一炮,乔美恬就更扯淡了,她居然打越洋电话要求跟我视频做,开玩笑,我可没那么好的想象力,也不想我的手太过劳累,一天光写文件签字它就够受的了。
但陈树是个例外。
第一次抱他的时候是在徽居,吃完晚饭我抱他上楼,他的身材好极了,触手柔韧温软,如同三月里抽芽的嫩草,带着让人艳羡的青春鲜活,散发着少年人特有的淡淡的体味,阳刚但不霸道,诱惑又不失纯洁。
很舒服,比抱着任何一个女孩都舒服,无论温度还是重量,都刚刚好,趁手极了。
很快我发现他喜欢我,同时惊讶地发现自己也喜欢他。
我喜欢他用清澈见底的眸子注视我,然后在我回视时匆忙移开视线。我喜欢他用克制的充满崇拜与欢喜的神态听我瞎掰,在我故意停下的时候抿一抿薄薄的唇角,低声问:“后来呢?”
这种感觉很美好,无关乎爱恋,只是随着直觉去享受某种微妙的喜悦,没有企图,没有欲望。
在那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对一个男性的躯体产生异乎寻常的兴趣,但当他偷偷跪在沙发边吻我的时候,欲念排山倒海而来,半梦半醒间我紧紧抱住了他,顺应他的邀请回应他的唇舌。
他满面通红几乎窒息的表情太过诱人,我几乎不能控制自己,差一点就想将他压倒在地毯上做点什么,但我没有,我不能想象如何进入他,像操弄女人一样对待他。
我不确定自己能坚持那个过程,真要那样做的话,我可能需要心理建设。
其实我低估了我自己,当那一天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犹豫。
我知道他病着,也感觉到他在发烧,一开始只想他用嘴帮帮我算了,但真正做起来的时候却无法停止,这不够,我想要他,彻底地占有他。
进入的时候他似乎哭了,虽然我喝了很多酒,神智有点模糊,但仍能清楚地感觉到他滚烫的身体有着轻微的抽搐。想要摸一摸他的脸,他却坚决地挡开了,我明白,他不想让我知道他哭了,尽管他心里委屈,尽管他疼的厉害,但他依然没有拒绝我的入侵。
我意识到他爱上了我,所以才心甘情愿地让我在他身上为所欲为,那一刻我的心有某处被溶化了,悸动的厉害。
我喜欢他,喜欢他的倔强,喜欢他的别扭,喜欢他的干净,我确定我是他第一个男人,这是我在以前任何一个女人身上都没有得到过的东西,我没有这方面的情绪,但,我珍惜他的纯洁。
以前跟过我的女人,我都会尽可能地对她们好,但那只是一种尽义务般的想法,再说我也要面子,但陈树不同,跟他在一起,时间越长我陷得越深,为他所做的一切都不再是尽义务,不再是顾面子,我发自内心地想要对他好,就如同他对我的那样。
他母亲去世后的那晚,我萌发了一种念头,我想要一直和他在一起,不是做爱,是长久的生活。
这念头真荒谬,但我越想越坚定,他比任何一个女人都适合我,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
为了这个想法我付出了很多东西,我的女人,我的兄弟,我数不尽的钱,还有我的名誉。爱情真是个可怕的东西,尤其对于我这种快三十岁才开始初恋的二愣子。可越是付出我越是开心,越是艰难我越是执着上。
陈树是个恬淡的人,衣食住行的要求都非常低,虽然他从来不要求我什么,也从没尝试过改变我,但我仍然被他的一些人生观潜移默化,办理离婚的时候,甚至产生了放弃锦泰的念头。
在阿华的运作下,我将尽可能多的一部分钱几次转手,通过风投投给了林柏凡的私人医院,暗股,股权书上没有我的名字,但我信任他。
接焉我用铁仔侄子的身份证件在开曼群岛注册了一个公司,然后和他做了些莫须有的生意,通过财务和证券将很大一笔钱转移到了那里。
尽管如此,锦泰仍然占我身家的三分之二。
没办法,有得必有失,只要我心甘情愿,只要我觉得值得就好。
“先生需要喝点什么?”空中小姐笑意盈盈地将我的思绪从纷乱的回忆中拉了回来。
“咖啡吧。”我说:“谢谢。”
“其实椰汁还不错。”身边的老太太忽然发话:“喝完了可以睡一觉,咖啡会让你兴奋,不利于倒时差哦。”
“那就椰汁吧。”我采纳了她的建议,老太太显然很高兴,冲着空中小姐眨了眨眼。
飞机飞的很平稳,商务舱的噪音也很低,单调的嗡嗡声中我有些昏昏欲睡,但又有点奇异的亢奋,三年了,除了一年半前他回国探亲,我们再没有见过面。
三年前的泰国之行是我人生中最凶险的一次经历,在曼谷分别的那个夜晚,我提着两桶方便面回到酒店,差点当场就疯了,我居然再一次把他给弄丢了!
我报了警,可全世界的警察都是一个鬼样子,面目可憎语气乏味,让我等满48小时再说,去他妈的48小时,48小时够我开车环游至泰国了。
在警局门口蹲了一宿,天亮了我才想起去机场接机。面对王喆我第一次心虚起来,他打我我也没还手。
我得捞到他,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后来我找到了他,当时他就站在那块巨大的褐色岩石边上,权念东用枪指着他,那一刻我的心跳几乎停止,他们离的太近,就算我现在拔枪也来不及了,他轻易就能射中他的要害。
我做了我一生中最傻的一件事,也是最不后悔的一件事——我就这么扑了过去。
时间和生命都定格在那一刻,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死”。
那天天很黑,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黑暗中什么也看不清,不然,我真想再看他一眼。
我以为我死定了。
不知道是什么神保佑了我,子弹擦着我的心脏飞了过去,贯穿了我胸腔,又射进了他的右胸,打穿了肺叶后卡在了他的肋骨上。
一个月后我醒了过来,一睁眼就看见ICU观察室的外面站着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是王喆。
他很快发现我醒了,换了无菌服走了进来,说:“你要是死了,那可是真是一尸两命。”笑了笑又说:“你他妈的命真大,这样都死不了,可见后福无穷。”
我费了半天劲才张开嘴问他:“他呢?”声音沙哑干涩,几乎听不清楚,王喆叹了口气说:“他还活着。”
两年前的骨折就伤了他的元气,再别提后来脑震荡和戒毒,他吃过的药都可以拿车装了,体质越来越差,经常无缘无故的低烧,抵抗力一直没有恢复。
医生在他体内取出了两发子弹,之后他一直炎症不断,身体时好时坏。
我们在泰国呆了快两个月,之后回了国,在S市的医院继续进行治疗。
九月末我们先后出院,他回到研究所继续读学位,我回公司面对董事会的集体指责。
我们的事情基本是公开了,我是无所谓,反正公司不大去了,一切交给阿华,估计年底我就会卸任,以后只做股东,半退休地养养身体就好。
陈树的压力比我大多了,权念东死后他的导师受到了一些牵连,手里的项目渐渐少了。再说研究所那个环境非常保守,同性恋这种事算是大忌,院领导陆陆续续找他谈话,要他去做心理治疗,又给他介绍对象什么的。
他那个脾气可想而知,温和的时候跟绵羊似的,真倔起来什么也不管不顾。他瞒着我交了辞职信,决定离开研究所。
关键时刻马库斯帮了他一把,通过自己在德国和瑞典的关系联系了一家德国高校,让他以交换留学生的身份做完剩下的论文,条件是毕业后留在埃斯利康工作五年。
我知道这事儿的时候马库斯已经帮他联系好了一切,他回S市来取证件,晚上第一次花钱在海滨酒店请我吃饱。
经过那么多事,其实他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他,但他很忐忑,跟我说的时候神情中带着愧疚。
“去吧。”我说:“我可以经常去看你。”
那天晚上他刻意讨好我,在我身下做出各种可爱的媚态,搂着我的脖子在我耳边呻吟挑逗。
因为身体一直没恢复,他的精神不算好,但那晚破天荒地主动,陪我做了一次又一次,最后我们连去浴室洗澡的力气都没有了,就这么脏兮兮地抱着睡了过去。
天亮后他又有些发烧,我想带他去医院,他搂着我的腰不让我动,趴在我身上又开始逗弄我。
“七年后我一定回来。”他说:“除了你我谁也不要。”
这是我听过的最动听的表白,七年算什么,七十年我也等得起。
再说我已经卸任,现在赋闲在家领分红,等身体养好了,可以去瑞典投资,开个饭馆什么的等着他,不知怎的我对开饭馆情有独钟,虽然自己不大会做饭。
飞机缓缓降落,我身边的老太太有些兴奋,她整理着自己小小的手袋,说:“噢,我终于到家了。”
我向她道喜,她说:“一个月后我还要回中国教书,但愿还能遇见你。”
收音机停稳了,我帮她取下行李,她向我道谢后拎着包包下了飞机。
在行李托运处排了一节短短的队后我拿到了箱子,拖着它往出口走去。
斯德哥尔摩比S市冷多了,从玻璃窗看出去,似乎也下着蒙蒙的小雨。
我停了步子,将搭在胳膊上的风衣穿上了,刚要抬步出关,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一路张望着走了进来,在一群金发碧眼高大状硕的欧洲人中间显得有些单薄,但身姿挺拔颀长,秀气而不失英挺。
大概是淋了雨,他身上的黑色短风衣肩头都湿了,柔软黑亮的短发有几绺贴在饱满的额头上,看起来有些孩子气。
他很快看见了我,薄薄的唇角向上扬起一个完美的弧度,冲我露出阳光般灿烂的笑容,快步跑了过来,漆黑的眸子一如初见时般清澈纯粹。
他曾经是我的男孩,现在,是我的男人。
雨还没有停,缠缠绵绵下着,从落地窗看出去,外面是一个小小的篮球场,有几个穿着卫衣的少年冒着毛毛雨正在打球。
陈树来斯德哥尔摩已经半年多了,一直住在这个公司分给他的小小公寓里,我曾经提出买一所房子给他,他不愿意,说太大了住起来麻烦。
公寓很小,但很整洁,和普通男孩不同,他的住处总是收拾的井井有条,任何东西都会摆在固定的位置,这方面他有着轻微的偏执,拾掇屋子跟拾掇实验室一样,恨不得给所有的柜子抽屉都贴上标签,职业病。
我抽完一根烟,掩上窗帘回到床边,他还沉沉睡着,俊美的眉眼半掩在松软的鸭绒枕头里,被子只盖到胸口,细腻雪白的皮肤上全是我留下的痕迹。
他还是老样子,一开始兴致很高,发泄完一次便情欲消退,昨晚虽然刻意打起精神来迎合我,但后面明显已经倦怠了。
算了,人无完人,这样也好,免得他总是兴致高昂,给自己的手增加负担。
“看什么?”原来他已经醒了,却闭着眼不起床,声音里带着慵懒:“再看是要付出代价的。”
他总是这样,话放的狠呆呆的,其实不见得很中用。
“我还有很多代价可以付出啊。”我掀开被子压在他身上,他的身体暖暖的,和三年前相比健壮了些,光洁柔韧的皮肤下有着一层薄薄的肌肉,虽然不甚强悍,但充满了力量。
他依旧很清瘦,身体线条流畅,宽肩窄臀,腰很细,大概因为经常运动的缘故,屁股却很翘,摸上去感觉好极了。
他的五官也长开了些,面孔开始有了刚毅的棱角,眉目间失去了少年的青涩,多了成年男人的内敛刚强,曾经看上去过分美丽的眼睛渐渐有了些沧桑感,但依旧清澈,依旧让我痴迷。
到底是年轻人,虽然昨晚半夜才发泄过,不过轻浅的触摸,两腿间的物体很快便精神奕奕。
“唔……”他皱了皱眉,雾蒙蒙的眼睛带着惺忪的媚态,挑逗地看着我,挺了挺腰示意我我他服务。
我握住他上下撸动,他舒服地哼了一声,右手探到下面来抓我,我躲开了,低下头吻他的唇,将他的舌头吸出来反复舔吮。
他的气息开始短促,搂着我的脖子在我身上磨蹭,我松开他的唇瓣,滑下去吻他光滑的下颌,一路在他脖颈和锁骨上留下更多的吻痕。
他的右胸有一个浅浅的伤疤,曾经有一粒子弹穿过了我的左胸,就是从这里射进了他的胸膛,差点要了我们两个人的命。
他注意到我的目光,也抬起手抚摸我右胸的伤疤,轻声叹息。
那噩梦般的一切都过去了。
怀着劫后余生般的喜悦,我吻住了他胸前的凸起。
粉色的小粒很快坚挺起来,硬硬的犹如珊瑚珠子,我用拇指按压,他浑身战栗了一下,喉间溢出低沉的呻吟,东西在我手中更加涨大。
他的脸都已经红了,酡红的颜色很快扩散到全身,看起来甜美而诱惑,我却停了动作。
他睁开眼,不满足地看着我:“干嘛……”
“我们来做个游戏吧。”我说:“看看谁更久一点。”
“你这人真是……”他有些无奈,又有些好奇:“怎么算啊?”
“用嘴的吧。”我取过手机调出秒表:“精确到秒,童叟无欺。”
“好啊,我们试试。”他来了精神:“谁先来呀。”
“你呀。”我按住他:“现在开始啊。”话音刚落便含住了他,他哼了一声,咬着牙说:“不要耍赖,你……慢点……”声音已经开始颤抖。
这个身体太过熟悉,每一处我都曾经爱不释手地细细品尝过,熟知他每一个敏感点,每一片一触碰就会引发呻吟的肌肤。
很快他就忍不住了,扯着我的头发让我跟上他的节奏,激烈地推送,片刻后射了。
我摁了手机,吻他的唇,将他的液体送进他嘴里,他喘息着躲避,从床的这头滚到那头,最终还是被我抓住了,弄了一嘴。
“你……”他恼羞成怒地踢开我,冲到浴室去漱口,我跟过去,和他挤在一起刷牙。
“什么味儿?”我问他,他瞪我一眼,可惜眉目含情,没有半点威慑力。
“才七分钟。”我笑着给他看秒表:“以后我叫你陈七公吧。”
“噗……”他喷了我一脸的牙膏沫,呛得自己直咳嗽,半晌才缓过劲儿来:“别得意,说不定你还不如我。”
“我有神功护体,你还不清楚么?”我洗了把脸:“哪次不是你先不行的。”
“那是我让着你。”他被我说中痛脚,狠呆呆地瞪着我:“延长时间也是为了我自己的性福。”违心的话一出口他就脸红了,却依旧絮絮叨叨放着狠话:“今天老子主场作战,一定让你丢盔卸甲!”
“来吧。”我摊开手:“就在这儿做,我站着,你有便宜占啊。”
他擦完脸扔下毛巾,做了几个滑稽的准备动作,按下秒表跪在了我身前。
论床上经验我比他要丰富的多,但嘴上功夫不相伯仲……呃……好吧,年轻人是要好学一点。
我真怀疑他GV看多了,要么就是专门练过,舌头简直比蛇还要灵巧,拼了命地在我最敏感的地带缠来缠去,力道轻重适宜,撩拨人的功力堪称一流。
到后来我都出汗了,他不依不饶地扣着我的腰不松手,眼含笑意地看着我,用嘴唇摩擦我,舌头轻触尖端。
我不知道自己坚持了多久,这种情况下每一秒都是极乐。
最后我抓着他的头发将他紧紧按在我身上,刺到他喉咙口,毫不怜惜地射在了里面,他呛了一下,眼睛都红了,百忙之中还没忘记按下秒表。
“燕小六。”他大笑着给我看手机:“六分半钟。”
我撇下手机托着他的腰将他抱起来,他的长腿自然而然架在我腰上,扯着我的耳朵叫:“干嘛,恼羞成怒啊?”
“对啊。”我将他扔到床上,压上去:“你这个妖孽,从哪儿学的这么多道道,爽死人不偿命啊!”
“这是老子自创的黯然销魂掌。”
“销魂嘴吧。”我啮咬他纤巧的喉结,他叫起来:“愿赌服输,不许恶意报复,你还没说赢了的人要怎么奖赏呢。”
“这就是奖赏。”我冲进他的身体,他哑声叫了一声,脖颈后仰,形成一个优美的弧度,抓着我的肩头颤抖:“你……好疼。”
我知道自己进去的猛了点儿,见他鼻尖都出了汗,忙停下来抱紧他,吻他的耳朵让他放松。片刻后他低下头看我,微微的晨光中眼神带着醉死人的幽怨。
“我好想你。”我心里一动,冲口而出:“我们结婚吧。”
他温柔地看着我,目光柔若春水,纤长的手指抚摸我的脸,我的胸口,什么话都没有说,身体轻轻动了起来。
后来我们又睡了一觉,醒来后他去洗澡了,我换上正装,静静站在窗前等他出来。
“你要去见总统吗?”他擦着头发走出浴室,微笑着指着我:“干嘛打扮这么英俊啊燕小六?”
我掏出一个盒子递给他:“我是说真的,咱们结婚吧。”
他迟疑着接过了盒子,打开来,眼睛一亮:“你……在哪里找到的?”
“我回了一趟泰国。”
他惊喜万分地翻来覆去看着那只表:“真的是那一只……我以为永远都看不到它了。”
我在泰国辗转很久才在一家二手店找到了那只表,好在它被保护的很好,没什么划伤。
“这样就想打发我吗?”他眼中含着水汽,语气却依旧俏皮:“哪有一只表送两遍的。”
“谁说两遍?”我抬起胳膊给他看:“上次送给你的表在这里。”
他没再追究,笑着将原本属于我的那只表戴在了手腕上:“好吧,便宜你了,得了我这么一个青年才俊,看在你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伺候我的份儿上,朕准了。”
“偷着笑呢吧?”我从口袋里掏出戒指,抓住他的手给他套上:“在这满地洋鬼子的地界儿,嫁个中国餐馆老板,是多么幸福啊。”
“你真要开餐馆啊?”他看着手上的钻戒,又拉着我的手看看,撇了撇嘴角:“你怎么自己戴上了,不是应该我给你戴的么?”
“我等不及了。”我笑:“说实话,喜宴的菜单我都想好了,你怎么跑的出我的五指山。”
“你这个霸道的家伙。”他拉着我的手,主动贴上来吻我。
细雨初停,阳光璀璨,新的生活,新的开始,爱,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