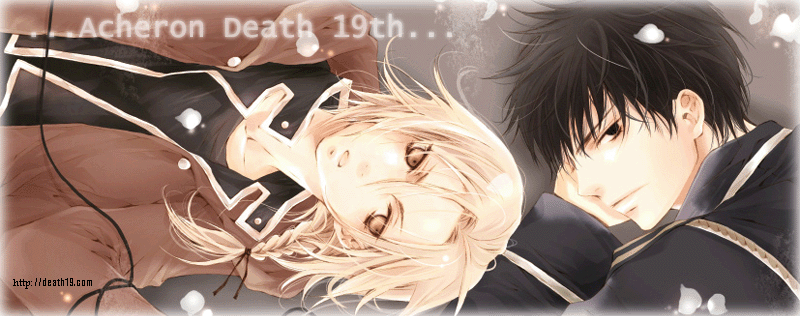番外 春的字典(上)
春感到非常『困扰』。
春查了字典里『困扰』的字义。朱批版的定义是『困扰:情感动词/名词,对自身的不理解/对他人的不理解。』而原版的定义是:『困扰:情感动词/名词,对眼前情况无法凭过去经验与现有智识加以解决时所产生的情感。』
对春而言,两种词义描述得都很贴切。都是『对的』。
春现在,确实对自己不理解。
眼前的情况也确实无法凭过去经验与现有智识加以解决。
而春同时,也对于现在『存在』在他身边的那个男人,彻底地,无法理解。
「你要盯我盯到什么时候?」春叹口气,出声。
春坐在房间的计算机前,右手边放着翻译稿,眼前放着日汉字典,左手边放着咖啡。
那是难得的新年连假。身为翻译没有年假可言,春手边有个急件,年后交稿。
本来春可以像以往一样,靠着熬夜与iphone里的『Forever Love』顺利完成工作。但那是春过往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现在春的身边多了个『东西』。
一个春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忽略的『东西』。
春把手从键盘上移开,转过来正对着困扰的根源。
「夏至恒,你该回去了。」春说。
春和夏至恒的交往,进入第三个月。
说实在话,春也不大确定两个人是不是正在『交往』。以前『交往』这个辞对春而言,就是两个人手牵手上街,一起吃饭、一起买东西,偶尔看个电影,仅此而已。
这是春第一次发现,他对『交往』这个词的词义,与人有着严重的歧异。
交往:动词/名词,两个人频繁『接触』的状态。
但春字典里的这个词义被蓝笔画掉,另外写上了:「交往:动词/名词,两个频繁以肉体『接触』的状态。」其中「以肉体」这三个字还放大书写。春没有笨到认不出夏至恒的笔迹。
夏至恒,想和自己做爱。
做爱。
春用单手掩住面颊。光是在心里想这个动词,或是名词,春便觉得自己的道德感受到了挑战。更何况堂而皇之地说出口。
更何况付诸于实行。
虽然春已经不算是处男了。不,应该说,在世俗的定义上,春还是个彻彻底底的处男,春的『枪管』没有被任何异性『使用』过。
但是就算不是『处男』,春想。这世上也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可以受得了有另外一个男人,每天跟在他身边,然后他说的做的想的行动的,赤裸裸的全带着上揭那两个字的符旨。虽然符征时有所变,但是内在意涵是一样的。
开始夏至恒先是用直叙法:『亲爱的春,我们来做爱吧!』
这文法遭到春把全裸的他裹棉被扔出窗去的酷刑,因此夏至恒改变策略。
夏至恒使用譬喻法:『亲爱的春,让我像枪管一般坚硬的OO进入你像枪套一样温暖的XX里吧!』
这文法一样遭到翻译家的唾弃,被处以睡地板之刑。
夏至恒于是使用象征法:『亲爱的春,枪管需要枪套。』
没有用,春认为象征法只是譬喻法的进阶。夏至恒一样睡了地板。
夏至恒锲而不舍,用了夸饰法和呼告法,试图以此激起读者的欲望:『春,让我的OO贯穿你的XX,在你体内炸裂,让你的灵与肉与我合而为一吧!』
很遗憾,夏至恒的文章激起的不是读者的欲望,而是读者的怒气。
既然作文章不奏效,夏至恒就改用行动表示。
现在春不管人在哪里,在做什么,回过神来都会发现放枪管的地方多了一支手。而且夏至恒只摸枪管也就罢了,这个男人熟知每一个让另一个男人燃起欲望的地方。夏至恒的手指出现在他耳垂上。颈侧上。小腹上。大腿间。嘴唇边缘。脚底板上。无所不在。
而且光摸也就罢了,春领教过无数次夏至恒脱人衣服的神技。现在两人既有『交往』名义,夏至恒更是能脱则脱毫不手软。
春就连跟他一起坐公交车,里裤都会忽然不翼而飞。更神奇的是外裤部份还好好的。
这让春烦不胜烦,他在一次忍无可忍下,拿尼龙绳把夏至恒五花大绑,打电话给丹。电话是上月初丹主动打电话来跟春联络时给的,要他把这个无耻的抢匪扭送警办。
『恐怕我办不到。』感觉丹在电话那头偷笑,『因为警察也正在找我。』
行动既然也被封锁,夏至恒不愧是夏至恒,职业的抢匪,完全没有放弃的迹象。
无法脱春的衣物,夏至恒就脱自己的衣物。
夏至恒有时会在春家留宿,和春挤同一张床。夏至恒有裸睡的习惯,这春在早先短暂同居的日子里已经知道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夏至恒就算不睡,也可以裸。
春已经不知多少次从书桌前回头,发现夏至恒脖子上挂着毛巾,光着结实形状完美的臀部,蹲在他刚买的冰箱前找可乐喝。或是从翻译社回家时,一打开门,看见夏至恒大腿开开地摊在角落看电视。大腿之间的东西不用明讲。
春总算知道,为什么当年恒春会拍到这么多亲哥哥的裸照了。
不是因为恒春喜欢,而是因为这是夏至恒『最好拍到的照片种类』。
春自掏腰包,替夏至恒买了好几套合身的长裤,勒令他至少在屋子里时布料覆盖全身比例要达到百分之五十。少百分之一都不行。
说真的,就算只有百分之五十的面积没有覆盖布料,春还是觉得困扰。但至少在可以正常生活的范围内,只是脸颊表面温度有点高而已。
连展现自身魅力这一招都被封锁,春以为,夏至恒这下子真的无计可施了。
但他低估了雄性生物在求偶期的执着。
夏至恒用『眼神』。
一开始春觉得夏至恒看就看,再怎么说,光看又不会掉一块肉。
但春很快就发现自己再一次错了。
以前春从来不知道,原来一个人的眼神也是会出声的。他会呢喃、会叹息。会窃窃私语、会谈笑风生。会声嘶力竭,会大吼大叫。
夏至恒走到哪里都盯着他看。走路的时候、坐车的时候,两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在路上逛街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刷牙的时候,喝水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甚至春坐在桌前翻译的时候,夏至恒都用同一种眼神,深深地凝视着他。
紧盯着他。
穿透着他。
撕裂着他。
而夏至恒的眼神传达的、吶喊的讯息,始终只有一个。
我想和你做爱。
亲爱的春,我想和你做爱。
春把脸深深地埋进手掌里,长长叹了口气。
搞了半天,他封锁了夏至恒的文法、封锁了他的触摸、封锁他的自我展演,封锁了以上种种符征。兜了一圈回来,夏至恒的原文符旨还是清晰直白地传达了给他,一点也没有哆译或错译的情形。
「夏至恒,我们得谈谈。」春终于妥协了,回到最原始的直叙法。
「嗯,你喜欢什么样的姿势?」夏至恒摆出认真谈话的态度。
春叹了口气。「这正是我要跟你解释清楚的。夏至恒,我不能跟你……你知道的。」
「做爱。」夏至恒提点他的漏词。
「夏至恒,我现在不能跟你做爱。」春放弃了。
「那『什么时候』可以?」夏至恒耐心地问。
「这个句子的重点不在『时间副词』。」春说
「总得有个『答案』。」夏至恒说。
「不是每个『问题』都会有『答案』。」
「我问春的每个『问题』,都有『答案』。」夏至恒一反先前的见解。
春叹口气。「等我可以接受的时候。」
「什么时候春『能够接受』?」夏至恒问。
「这是个『坏问题』。」
「『坏问题』也可以有『好答案』。」夏至恒一反先前的见解。
春发现夏至恒不知不觉靠得『更近了』。
危险。春不动声色地往后挪开,远离夏至恒的荷尔蒙放射范围。
「总之,现在不行,我还做不到。夏至恒,你不能够逼我。」春说。
「可是我们已经交往三个月了。」春既退到底线,夏至恒也摊牌了。「你想让我一直等下去吗?亲爱的春。凡事总得有个时间,你不能一直逃避下去。」
「我和前女友交往六年,和前前女友交往一年,我们都没有……」春再一次词穷。
「做爱。」夏至恒毫不犹豫地提词,「那是因为『你不爱她们』,春。」
「我喜欢她们。」春说。
「不,你不喜欢。春,我『知道』你的想法。」夏至恒嗓音温柔,用句强硬。
「我喜欢她们。我『曾经』喜欢过她们。」春同样强硬地说。
「春,亲爱的春,这不是句子使用过去式或是现在式的问题。」夏至恒略带无奈地说着,「你误解了『喜欢』的定义,或许你可以翻翻你的字典,看看权威是怎么说的?」
春真的翻开字典,查了『喜欢』的词义,「喜欢:动词,义同和我亲爱的夏至恒上床。」原本的定义和红笔改过的定义全都被划掉了,用蓝笔改上这样的字样。
「啪」地一声,春狠狠阖上他的字典。
「字典上怎么说?」夏至恒好整以暇地问。
「夏至恒,你可以玩弄文法,但不能左右我。」春再一次退回『底线』,「我『现在』确实喜欢你,但是那跟我『现在』想和你……」
「做爱。」
「不需要你提词,我刚刚正要讲那两个字。我『现在』喜欢你,跟我『现在』想和你做那种事,是两回事。我……我还没有准备好。」春说。
「春,你要准备什么?」夏至恒再一次靠近春,春这回真的背靠『底线』了。「你确实喜欢我,这我『知道』。人不可能喜欢一个人,同时却又对他的肉体感到反感,『喜欢你』和『讨厌你的身体』,这两个命题本身是二律背反。春,你讨厌我的肉体吗?」
春看着夏至恒。夏至恒不知何时又在他面前脱了上衣,只有上衣没有违反覆盖率的约定,春无法将他从窗户丢出去。
结实的上臂。
起伏有致的胸膛。
彷佛随时能将人掐到窒息的有力前臂。
潜伏自胸肌间,醒目而深邃的两枚蓓蕾……
春移开了视线。
「你受我的肉体吸引。」夏至恒满意地任衬衫挂回胸膛上,「春,你喜欢我的人,也喜欢我的肉体。真正的『喜欢』就是这样,我的灵魂不在时,春会思念着我的『存在』,春会『想象』我的存在。而我的肉体不在时,春会思念着我的『碰触』,春会『想象』我的碰触。这是一种自然而然、从灵到肉都想完全拥有对方的感觉。」
『一点都不需要准备。』——夏至恒缓慢地对着春说。
春保持着别开视线的角度,「我不像你。我不会把别人写下的定义从字典里划除,以为他人理所当然地须接受我写下的『定义』。『喜欢:动词,尊重该动词所指涉受词对于『喜欢』的定义,并加以配合。』这才是我的『定义』,夏至恒。」
夏至恒苦笑。「春,我们每次都得来上这么一段吗?别的情侣都嫌言语交流太少,我想我们是太多了。或许我们该尝试『无声』地来做点什么。」
「总而言之,我办不到。」春叹口气,「别逼我,夏至恒。」
「怎么会,春『曾经』办到过不是吗?」夏至恒跪直在春面前,如同羔羊,「那就和『曾经』那次一样就好。春,把一切交给我,我保证会让你睡得比一年前更好。」
春的颊再次烫如火烧。水泥格子里的记忆『又回来了』。
「好。」春说,夏至恒喜出望外,「前提是,句子的主受词互换。」
夏至恒一怔,「互换?」
「『夏至恒上了春。』这个句子主受词互换。」春说。
「像是『春被夏至恒上』这样吗?」夏至恒从善如流。
「那是『倒装』。」
「春,亲爱的春,这是个严肃的问题。但我想我们可以解决。」夏至恒的声音很温柔,「春确实渴求着我的肉体,对吗?」
春瞥了一眼夏至恒敞开的衬衫,摇头。
「那就没有问题了,春。我以过来人的身分向你打包票,这个句子无论正装或倒装,结果都是一样的,一样都是美好的句子。也一样能够达到我们渴求彼此肉体的目的。」
「那是因为你没有『疼痛』过。」春扳着脸说。
「春,如果是这件事阻档了你对我肉体的渴求,我可以保证,今晚你绝不会再累积相同的经验。那是第一次,我难免有些急躁。」
夏至恒的眼神如醇酒,诱人至深。「我会对春很温柔的。」
春在夏至恒的唇几乎贴上他的瞬间直起身,窜下床。脚踏垫取代春跳到床头。
「我要出门了。」春收拾床上的文稿。
夏至恒浅浅叹息。「去哪里?」
「去翻译社,找我的责任编辑。」春说。
夏至恒跳下床,追上在门边拿大衣的春。「为什么又去找他?春上周才去过不是吗?」
「上周是交稿,这次是讨论新工作。责编说有间出版社看了我翻译的文章,打算让我试试看翻译小说。」
春简短地说,打开门。没想到还没踏出门一步,手臂就被人抓着拽回来。夏至恒的掌心压在春身后的墙上,那张脸靠春好近。
「春好常去找你的责任编辑。」夏至恒说。
春翻白眼,「他是我的责任编辑。」
「春总是不自觉地对人温柔。还是那种『在这世上我只对你如此』的温柔,这种温柔让人产生错觉。」夏至恒说:「春的温柔,太容易让人产生错觉。」
春试着扭过身,被夏至恒抓住前臂扯回来。夏至恒甚至把春整个转过来,从后面夹住春的双臂。
春动弹不得。
「把春关起来就好了。」夏至恒做出『假设』:「把春的双手双脚绑起来,锁在笼子里,只有我能够看见春照顾春。这样春就会永远留在这里。永远『存在』在这里。」
春缄默。「夏至恒,我只是要去我的责任编辑那里。」
夏至恒的手臂收紧。
「阿春也说要去找他的复片师。」夏至恒笑笑,「他笑着跟我说再见,还交代晚餐炒饭不要煮太咸。下次再见到阿春时就是在河里,就是『那种东西』。」
春感觉有什么往他『那里』刺了下。「我不是『恒春』。」
「要是我当初这么做就好了。要是我拉住他,把他关起来,不让他出门就好了。都是因为我让阿春出门。我毫不在意地和他说『再见』,甚至没有多看他背影一眼。所以阿春才会变成『那种东西』,都是我不好。」
「夏至恒。」
「我不会重蹈覆辙。不想重蹈覆辙。我不要春变成『那种东西』。」
「夏至恒。」春拉了夏至恒的手臂,试图挣脱。夏至恒忽然手腕一翻,翻出一把五公分长的刀片。春在某一个晚上曾看见夏至恒在他床头把玩,春还以为他是要拿来刮胡子。刀片抵住春的脖子,抵在颈动脉上。『太近了』。
春停止呼吸。
「夏至恒,把刀子放下。」春冷静。
「是春不好。」夏至恒沉默良久,笑笑。「春太过温柔。春轻易地『接纳』了我。明明知道我是银行抢匪,我拿着枪冲进银行,用枪管抵着他们经理的头,威胁他们不给密码就杀死人质。我做过这种事。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连自己会做出什么都不知道。」
「抢银行的不只有你。」春说:「我也有『参与』。我是『共犯』,夏至恒。」
「春对我一点防备也没有。」夏至恒拿刀的手微微颤抖,「毫无防备地让我亲近,毫无防备地在我眼前睡着。」
『我很可能会杀死春。』——夏至恒几乎用气音在春的耳壳旁呢喃。
春试着再挣了下。夏至恒放开手,刀片离开春的颈子。
「我要出门了。」春说,「我会回来,等我回来。」
春走出房间,无法忽视夏至恒从背后一路凝视的目光。
*
春找到责编,和他聊了小说翻译工作的梗概,喝了两杯茶,聊起近况。
「如果有人拿刀抵着你的脖子,说要把你监禁起来,你觉得怎么样?」春问责编。
责编沉默良久。
「春,内政部警察局的报案电话是110。」责编说。
「那个人前一秒钟还想尽办法千方百计要跟你上床。」
「打110时记得顺便通报社会局,他们会派性侵害防治中心的人替你验伤。」
春叹气,「那个人是我现在的交往对象。」
责编陷入死寂。
「春,我知道和交往六年的女友分手对你打击很大。」责编挪动硕大的身躯,两手按在春的肩头:「但你也不能自暴自弃。天底下好女人还是很多的。」
「或许他只是想跟我上床。」春自语着,「他很『不安』,我感觉得出来。」
「春,其实单身也是很好的,你还有我在。」
「我应该跟他上床吗?」春转头看着责编,「我跟他做那种事,就能消除他的不安吗?这会是个好的『答案』吗?」
春本来以为,夏至恒多半会去哪里躲个一两天,好化解尴尬。这个男人总是如此,春还特地去图书馆借了万城目学的新书,准备在夏至恒『不存在』的期间消化。
但是令春惊讶的是,夏至恒一如往常。在接近晚餐的时间来找春、坐在床头看春翻译、和春去吃晚餐、回到房间和春一块看电视,兴致来时和春一起走到车站。假日来临时相偕去看展览,白天偶尔通通电话。
唯一不同的是,夏至恒似乎『放弃』了。
他不再提任何和春『做爱』的事。
口头上当然没有,在春家留宿时,也会好好地穿上长裤。春的贴身衣物不再不翼而飞,连在街上散步时,夏至恒都会刻意离春一公分距离。
有一次春从浴室洗澡回来,绊到了门坎跌了一跤。夏至恒以惊人的速度从床头移动到门口,用手托住春的腰把春接住。春的视线对上夏至恒的视线,『看起来完全像是要吻他』,春甚至已经『想象』到夏至恒吻住他的画面。
但夏至恒没有满足春的『想象』。他放开了春,坐回床头研究他的计算机。
连看他的眼神也变了——春无法不注意到。先前那种赤裸裸的欲望,春每被夏至恒看一眼,就觉得少了一件衣物。
但现在夏至恒看他,就像在看那条小巷里的女性朋友。即使两个人眼神擦过,也没有任何火花。友爱至极。『道德』至极。
『做爱』两个字似乎从『夏至恒词典』里彻底删除了,春猜不透哪位借阅的读者做了这种好事。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年假将近,夏至恒完全脚踏垫化。
而脚踏垫至少还会蹭春咬春,夏至恒连春的一根手指也不多碰一下。
春开始坐立难安。
春开始有意无意暗示夏至恒。
春在吃饭时和夏至恒坐在同一边,好让手臂抵着夏至恒。在坐公交车时挑选双人座,好在睡着时把头若无其事地搁在夏至恒肩头。春从淋浴间出来时刻意不穿上衣,在夏至恒面前光着上身翻找衣柜。这已经是春所能做到『不道德』的最高极限了。
但是没有奏效。
春试着用『隐喻法』:「含羞草被人触碰就缩起来,是因为一下子受到太强烈的刺激所致。如果从根茎开始缓慢的抚摸,含羞草就不会出现那种反应。」
夏至恒:「我对Discovery没有兴趣,亲爱的春。」
春试着用『倒反法』:「最近你做的很好夏至恒,完全符合社会大众对一个情人应有的期待。你还能做得比这更好一点吗?」
夏至恒:「多谢,我努力。」
春试着用『层递法』:「多做不如少做,少做不如不做,不做又不如适时地突破。」
夏至恒:「春,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春越来越焦躁。夏至恒越来越冷静。
「夏至恒,我们得谈谈。」春终于忍不住了,回到最原始的直叙法。
春番外 春的字典(下)(End)
「夏至恒,我们得谈谈。」春终于忍不住了,回到最原始的直叙法。
床头上的夏至恒停下打字的手。
「我穿着衣服,也没有脱春的衣服。」夏至恒说。
「所以我想跟你谈谈。」
「我没有乱摸春,也没有用春讨厌的眼神看春。」夏至恒说。
「我正是要跟你谈这件事。」
「我喜欢春。我爱春。所以我尊重春的决定,春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夏至恒说。
「夏至恒。」春叹了口气:「你一定是故意的。」
夏至恒的视线从计算机上抬起来,「为什么这样说,春?」他的声音无比温柔。
春感到局促。「我没有要你这么做。」
「怎么做?」夏至恒的手还搁在键盘上:「我不懂春指的是什么。」
「就是……你知道的。你『知道』我的想法。」春说。
「春不想和我上床。」夏至恒说:「所以我尊重春的『想法』,有什么不对吗?」
「我没有不想跟你……做那种事。」春显得尴尬,「我只是,想慢慢来。我需要时间,夏至恒,就像我之前说的,我需要一点准备。」
「所以我给春时间『准备』。」夏至恒说。
「你『改变』得太多。」春的脸颊开始发烫,「你不能忽然改变做法,我是说,你改变得太多且突然,这让我混乱。你的『定义』和以前不同,连带对你的『分类』也无法确立。我无法如同过往一样『认识』你,更遑论『相信』你。」
「那么春想要我『怎么做』呢?」夏至恒说:「春不想跟我做爱。春『现在』不想跟我做爱,这个陈述是正确的吗?」
春无法摇头,只好点头。
「春不想跟我做爱,却允许我『至少做些什么』。」
夏至恒说:「我被允须牵春的手、搂春的腰。我被允许碰触春的身体、用赤裸的眼神看春。我被允许亲吻春、舌吻春。我被允许观看春的裸体、把自己的裸体给春看。春允许我做这些事,春允许我『只做』这些事。这就是春真正的『想法』。」
不公平。
春的脑海里浮出这个句子。
春无法否认这个句子。
「没有『不公平』。」夏至恒说:「春选择只想『碰触』,是因为春可以接受。但我无法接受,我无法只『碰触』而不『占有』,所以我选择连『碰触』都不做。『是我太过喜欢春』,这是我自己的责任,春不必为我担负那个责任。」
『所以我会忍耐。』——夏至恒望着春的脸说,然后把视线转回计算机上去。
春沉默下来。握拳,咬唇。
「夏至恒。」春爬上了床,坐到夏至恒身前,「我……或许我可以试试。」
夏至恒几乎是立即关上膝盖上的计算机,啪地一声。「试试什么?」
春觉得自己正在『被拖进去』。他无能为力。
「试试看和你……做那种事。就是你说的那个……」
「做爱。」夏至恒毫不犹豫地提词,春发现他的腰被从后头揽住了。「春『现在』想和我做爱,这个陈述正确吗?」
「我是说『试试看』。」
「春『现在』想和我做爱『试试看』。」夏至恒修正句子。春发现夏至恒放下计算机,抓住春的右手臂,久违的『接触』让春脸颊又烫起来。
「我先去洗个澡。」春开始后悔。
「我不想勉强春。」夏至恒看着春说:「我可以继续『忍耐』,忍耐个一年,或许到明年的耶诞夜。」
春放弃了。
春爬上床,以壮士断腕的速度脱了上衣,露出赤裸的上半身。
「慢着。」夏至恒抑止唇角的扬动,「春不是想要『倒装』?」
春开口,唇齿干涩。「是『主受词互换』。」
「那么。」夏至恒放开握住春的手,仰靠回床头,「我尊重春的『想法』。」
春眨眨眼睛。「你说真的?」
夏至恒摊开双手,末了右手往领口一扯,自行解开了领口的扣子,一路解到锁骨以下的位置,用仰角看着春。
「春,吻我。」夏至恒说。
春感到晕眩。
房间一夕之间旋转起来。不是『譬喻』。春体内大部分东西都涌到脸颊附近:血液、氧气、热量、盐酸。独独只缺水分,春的喉咙干到燃烧起来。不是『夸饰』
春四肢并用,凑近夏至恒。
春的唇离夏至恒的唇只有一公分。
夏至恒没有闭上眼睛。
春吻了夏至恒。
春是主词,夏至恒是受词。吻了是及物动词过去式,代表义无反顾。
春的唇和夏至恒分开,任由唾液淌下。春发现夏至恒仍旧没有动作。春的耳朵里嗡嗡作响,四肢末梢都在发抖。春用两手捏住夏至恒的衣领,膝盖撑住身体,喘息。
「夏至恒。」春用细微的声音叫他,催促他『造句』。
『夏至恒托起了春的下巴。』
『夏至恒吻住了春,把舌头伸进春的口腔。』
『夏至恒在床榻里压倒了春。』
『夏至恒对春OOXXOOXXOOXX……』
诸如此类的句子。
「春。」夏至恒笑笑,「你是『主词』。」他提醒春。
春从脸颊涨红到了脖子根。
春回想着,过去看过有关『枪管』的影片。但即使是影片,春对『枪管』的认知也屈指可数。春对『军事活动』不感兴趣。更何况多数军事片,谈论的是男人的『枪管』与女人的『枪套』,没有人探讨两个拿枪管的男人碰在一起该怎么办。
春搜枯索肠。他再一次吻了夏至恒,想起夏至恒平常吻他时总会伸出舌头,春伸出舌头,却发现夏至恒紧闭着唇。
春感到恼怒,知道夏至恒『在模仿他』,春总是紧闭着唇,直到夏至恒主动拉住春的后脑杓,用舌尖撬开春的唇,恣意抢夺。
春吻得唇齿发疼,做为『受词』的夏至恒却没有任何反应。
春解开了夏至恒的衬衫。
春吻了夏至恒的锁骨。
春伸手解开夏至恒的裤头。
春的指尖触摸着夏至恒的腰线。
春把唇凑近……
春发现,自己忽然不会『造句』了。
「怎么了,翻译家。」夏至恒靠近春的耳壳,声音柔和,「需要我为你思考下一个『以春为主词』的句子吗?」
春抬起头,眼眶热得发疼。
夏至恒伸手触碰春的下颚。
夏至恒的指尖抚摸春下巴的凹陷处。春看过夏至恒以同样的方式抚摸脚踏垫,脚踏垫最近完全被夏至恒的爱抚怔服,整天腻着夏至恒的大腿不放,被夏至恒的手法弄得一脸酥麻呼噜呼噜个没完。脚踏垫是公猫。
春忽然可以理解脚踏垫的『感觉』。
「春总是很聪明。」夏至恒持续抚摸着春说。春露出不解。
春总是很聪明。
通常要夸另一个人聪明,会说『某某人很聪明』,或是『某某人在某些地方特别聪明』。总是很聪明,频率副词Always不该放在人格特质形容词上,这是错误的文法。
「就像现在这样,春。」夏至恒笑出声来,「春总是很聪明。虽然有些地方呆呆的就是了。任何聪明人都有空缺的时候,越是看起来聪明的人,空缺的时候就越多,这是我在银行——不,是诈骗集团工作下来的心得。有些人自诩聪明,觉得这世上除了自己以外都会被骗。他们聪明但不思考,多数聪明人都以为自己聪明到无需时时思考。」
夏至恒抚摸春的手,不知不觉移动到了胸口。
「我第一次在展场遇到春时,就觉得这人是不是三百六十五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思考。如果一年有三百六十六天,春会连多出的一天都拿来思考对吧?」
「闰年就有三百六十六天,无需『假设』。今年就是。」春说。
夏至恒笑起来,咯咯笑个不停。「啊,春,亲爱的春,我真喜欢你。」
春脸颊发烫,心跳加快,不明所以。
「春的字典里没有『理所当然』、『显而易见』,更没有像『这种事情连三岁小孩都知道』这种句子。对春而言,每件事都需要推敲、都需要思辨。春的脑袋没有『空缺』,所以春『总是很聪明』。」
夏至恒的手挪到春的裤头。
「这让我感到棘手,非常棘手。」
夏至恒苦笑,「春这种人,是我们诈骗集团的『天敌』。」
喀当一声,春裤头的扣子被解开了。
「在找春当伙伴、和春『计划』的期间,我一直觉得自己『被看穿了』。拥有『知道他人想法』、『支配他人想法』能力的应该是我才对,明明是我才对。但我却有春对我的一切了如指掌的感觉。『我骗不了这个人』,春的眼睛一直这么告诉我。」
「我并不『认识』你,那个时候。」春喉咙干燥。
「但春也因此不『相信』我。」夏至恒笑笑,「春或许不知道,先『认识』而后『相信』,对春而言严谨的逻辑步骤,多数人却无法遵守。春比自己认为的聪明得多,春比自己想象的『知道』得更多。所以到最后我有点怕你,春,你令我感到敬畏。」
春一怔。
春的翻译,令人毛骨悚然——依稀有人这么说过。
毛骨悚然,和敬畏。春分不清哪一个比较让他五味杂陈。
「春拥有自己的字典。」夏至恒继续说着,「春为每件事情下了自己的『定义』,自己的『分类』。包括喜欢、讨厌、困扰、同情。包括交往、接吻、爱抚、做爱。包括春的前女友们,包括春的责编,包括丹、包括我。包括『夏至恒』。」
夏至恒的手滑下春的背脊,停在春的腰线。
春稍微挣了下。换来的是夏至恒反过身,抓住春的手臂,春被压着反靠到床头,换夏至恒跪坐在他面前。
「但是春的字典里,少了『一个词』。」夏至恒说。
「少了什么?」春忍不住问。
夏至恒对着春微笑。
「少了『春』。」
夏至恒轻声,「少了你自己,春。不信的话,你造几个『例句』试试?」
春被夏至恒压在床板上。
春的脸颊被夏至恒吻了。
春的大腿被夏至恒的膝盖抵住,缓慢地磨蹭。
春敞开的裤头被夏至恒的手伸入,覆住了『那个地方』。
春被夏至恒……
春试着造了几个『倒装』的例句,以证明自己的字典没有缺漏,但越造越是支离破碎。只因夏至恒靠得他『太近了』。
春被迫停止造句。停止思考。
「春的名字,用日文叫起来是什么?」夏至恒忽然问,在春的耳边低声。
「你要知道这个做什么?」春声音细微。
「好奇。」夏至恒露齿一笑。
「HARU。」
「哈啰?」
「HARU,春天的意思。」春瞪了夏至恒一眼。
「哈噜。」夏至恒深情地叫着。
春噗嗤一声。
春很快便无法再笑。夏至恒伸出手,再一次触碰春的下巴深处。
春闭上眼睛,四肢往躯壳缩拢。夏至恒呼出的热气喷在春的眼睑上。
「『哈噜』好紧张。」夏至恒笑起来,「为什么这么紧张?」
春简直想杀死眼前的男人。
「我也很紧张。」夏至恒说了令春意外的话:「不信,春可以摸摸看。」
夏至恒拉住春的手,把春的掌心贴到自己胸口。
心跳声快得令人吃惊,令春吃惊。
这么烫、这么热、这么快。却又如此有力。
春发现自己爱上夏至恒的心跳声。
「『春』想和我做爱。」夏至恒忽然说。
春蓦地抬起视线,和夏至恒四目交投。
「春想跟夏至恒做爱。」夏至恒又强调了一次,「春很想被夏至恒上,春渴望夏至恒上他。这是春的『想法』,我知道春的『想法』。」
「这不是我的『想法』。」春低喃着。
「好吧,这不是春的『想法』。」夏至恒笑了,「是我『支配』了春的想法。记得吗?我拥有支配春想法的能力。所以这不是春原本的想法,纯粹是被我支配所致。春想和夏至恒上床,想得不得了,春,现在我『支配』你这么想。」
春现在完全相信夏至恒有那种『能力』。
因为春的全身,又像那一晚在水泥格子里一样,到处疼痛起来。
「春想要我抚摸他的乳尖。」夏至恒持续支配着下流的『想法』。
春的乳尖果然开始发疼,覆盖的布料早已被夏至恒剥除。夏至恒的指尖拈上春的乳尖,用指腹搓揉。『真不公平』。
春的呼吸乱了。
「春想要我把舌头放进去,舔春的舌头,磨擦春的牙齿,把唾液搅进春干涩的口腔里。」夏至恒支配的『想法』巨细靡遗。
春的喉咙果然开始干燥。夏至恒的唇吻上春的唇,舌头撬开春紧闭的唇瓣。舌尖长驱直入,搅乱了春口腔里所有的氧气。
春无法呼吸。
「春想要我抚摸他的『枪管』。从根部开始,到顶端的位置。春想要我用掌心搓揉,由慢至快,最后用大姆指在出口的地方磨擦,一直到春想要射出来为止。」
夏至恒伸进春里裤的手动了。动得比春的『想法』更激烈。
春动弹不得。
「春想要我把手指插进春的后面,我的手指会涂满润滑油,先从指尖开始。春想要我慢慢地增加手指,一根、两根、三根。直到它充分良好地被扩张。」
春遮起耳朵,拒绝再听夏至恒对他想法的『支配』。但是没有用。
夏至恒托起春的腰,让春的颈子挂在他的肩上。春的里裤兼外裤早已不翼而飞,春一如往常不知道是何时和它们分离的。
春的后面感受到夏至恒的『触碰』。
春呜咽起来。
「春想要些微的疼痛,」夏至恒很快接口,就在春的耳边。「一点点无妨,春喜欢这样。春知道疼痛能够增加情趣,情趣很快就会转变成至高无上的快感。春想要我的手指在里头慢慢地动,磨擦春里面的敏感点,直到春习惯。」
「别说了。」春喘息。身体的感觉夺走春所有思考能力,春无法思考,夏至恒值入的『想法』取代了春的思考。
春被『支配』了。
「春想要我在触碰到正确的点时屈起指节,一根、两根、三根。春想要我用指甲在体内搔括,春想要我反复地碰触敏感点,在我的碰触下喘息,在我的碰触下颤抖,在我的碰触下哭泣,春想要在我的碰触下高潮……」
「别说了……」春的嗓子开始带着哭音。
夏至恒翻过了春,让春的后脑枕在枕头上,他依旧抬高着春的腰,却拔出触碰春体内的手指。夏至恒把手指拿来做别的用途,他解开了自己的长裤。
春看见了夏至恒的『枪管』。
说实话,这不是春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见夏至恒的『枪管』。拜恒春那些照片之赐,春早已从各种角度拜见过这支型号的『枪管』,熟知他的形状、长度和口径大小。但是现在这支『枪管』,却和春过去熟知的口径完全不同。
春用双手掩住了面颊。
「春想要我凝视他的表情,无论疼痛、忍耐、哭泣或欢娱。」
夏至恒笑着移开春的手,用『枪管』前端碰触春。春咬住下唇。
「春想要我进去。」夏至恒的嗓音搀入了喘息:「春想要我的『枪管』,狠狠插进春的后面,把春的那里尽情地撑开。」
夏至恒挺了腰。
春闷哼一声,眼眶开始湿润。
「夏至恒……」春干哑着。
「春想要叫我『小夏』。」夏至恒柔声,「春想要一边呼唤我的名字,一边让我把整支巨大的『枪管』埋进去,用最坚硬滚烫的部份磨擦春、撞击春,直到春受不了向我求饶为止。直到这支『枪管』射击为止。」
春那张八十公分宽的床开始剧烈摇动,脚踏垫惊慌地窜逃到地板上。
春张口呻吟。呻吟变为叫疼。叫疼变为一串串细微的啜泣,「小、小夏……」
「春想要用这种方式和我结合。春想要和我的灵魂与肉体结合。春想要我的一切,如同我想要春的一切。春想要我,想要夏至恒。」
夏至恒的声音包裹着春:「不论多久、不论多少次……」
无论夏至恒怎么『支配』他的想法,春都绝对不会想『再多一次』。
春在失去意识前这样对自己发誓。
*
春过了三天,才有从柔软的地方爬起来走动的『想法』。
夏至恒的『支配』能力无敌且强大,春这回切切实实地领受到了。
特别是在春被夏至恒蹂躏一回,呜咽着说想休息时,只因为夏至恒在他耳边低声『支配』了什么:『春还想要,春还想要夏至恒第二次。夏至恒这么迷人,春做多少次都不够。』春便又胡里胡涂地放任夏至恒做了第二次。
还有第三次。
还有第四次。
第五次以后,春已经放弃计数了。任由自己沉浮在夏至恒支配的『想法』中。
真是太可怕了。春绝望地用手托住了面颊。
夏至恒这几天心情奇佳,在春的床榻边转悠,嘘寒问暖、好事做尽,反过来被春『支配』,完全以春的想法为自己的想法。
春转过头,夏至恒就在他脚边,枕着他过去专属的枕头,侧着身,布料覆盖比例一样只有百分之五十,在春天的阳光下睡得正沉。脚踏垫靠在夏至恒的小腹上,刚经过夏至恒一轮技巧高超的爱抚,一样睡得心满意足。
春叹口气,想起昨天责编给他捎来电话。
『春!』责编的声音听起来气急败坏,『有人寄了『裸照』到我电子信箱!』
春的心脏一撞,『裸照?』
『对!而且还是男人的!』
『你认识那个男人?』春谨慎地问。
『不认识,应该说不知道认识不认识,那些裸照什么部位都拍了,就是不拍脸,真是气死人了!』
责编忿忿不平地说着:『不过从身材看得出来是同一个人,男人有这么好身材的还真是不多,胸肌很漂亮、大腿和手臂都很结实、背脊的弧线美得像修图,更气人的是那个腹肌!怎么有男人的肚子可以紧实成那样!真是太没天理了,那还是个男人吗?』
春松了口气,那显然不是『他的裸照』。
但春也很快知道那是『谁的裸照』,不由得在电话那头苦笑。
『除了裸照,还有其它什么入镜吗?』春问:『像是他身边的房间摆设,或是他正在和什么人做什么事之类的。』
『没有,就只有裸照,而且还是自拍。春我跟你说,那个男人肯定是个超级大变态,有一张是『那玩意儿』正对镜头,还用鱼眼镜头做特殊效果。搞什么鬼,挑衅人嘛!就算『那玩意儿』大一点又怎样?真想让他知道什么叫男人的重质不重量!』
不,『那玩意儿』既有质又有量。春掩着发烫的脸颊想。
『春,怎么办,这会不会是他想向我暗示什么?』责编担忧地说:『他是不是对我有兴趣?春,你说我会不会有危险?我该拿那些照片怎么办?』
『把它们删掉。』春面无表情地说,挂断了电话。
春看着在地板上熟睡,唇角还挂着一丝浅浅笑意的夏至恒,拿起桌上的字典。
『夏至恒:人称专有名词,春的交往对象/令春困扰的男人/银行抢匪/诈骗集团/身材很好的男人/喜欢全裸的男人/善于支配他人想法的男人。』
这行词义是春用铅笔加上去的,春写在字典的折页里,没有让夏至恒发现。
春拿起铅笔,在定义下又加了一项:『爱吃醋的笨男人』。
春放下铅笔,随手翻着字典,发现其中一页不知道被谁折了角。
春掀开那页,微微张大了眼。
那页的词汇正是『春』。原本的定义是『春:名词,四季的起始。』而不知名朱批版的定义是:『春:名词,四季的起始,情欲的象征/希望的象征/重生的象征。』
而现在这些定义通通被划除,以熟悉的笔迹这样写着:
『春:人称专有名词,只有夏至恒能定义的人。』
春先是哑然,然后苦笑,最后抿着唇浅浅地扬起唇角。
春把字典阖上,搁在夏至恒的枕旁,俯身趴在他身边。看样子得换一本新的字典了,春把头靠在夏至恒的肩膀上想,在春天的暖阳下满足地沉入了梦乡。
—番外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