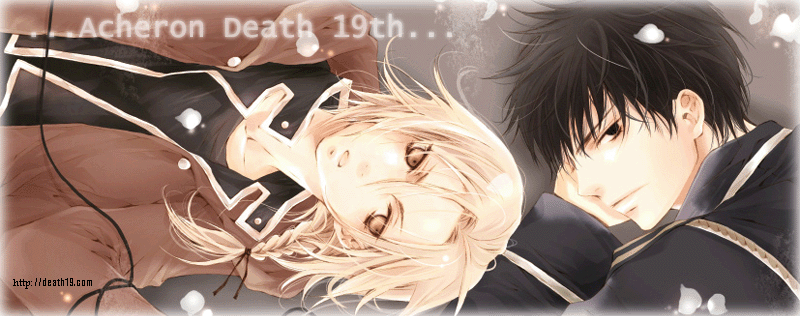另一版结局,修改后,不过依然是BE
万岁第六十五声
这些日子都睡得很不踏实,半夜乍醒多次,半梦半醒间一切都似真非真,假亦非假,楚桑被困在梦魇里,脑子里却越发清明,那些微小琐碎,甜蜜欢乐,甚至生死别离间的事一一入梦,静滞不走着。
他用力挣扎,喘出一口粗气,手啪的一声按在了心口上,一下子终于睁开了眼皮。
心不在此,又谈何安眠。
他开始恼火自己的多愁多忧,这种软弱来的太不是时候,他应该站得更挺直一点,把天再撑高一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怯弱下去。
冷雨持续不断的下了几个昼夜,刷得宫里空气都稀薄了几分,凉意润过了头就渗到骨头缝里头去了,倒是花园那些佳木葱茏不惧寒意,越发青郁,近处紫藤蔓蔓缠缠在云木上,香风密叶,枝蔓婆娑。
“皇上今早在胜湖那儿喧了礼部的几位大人,上皇您看……”
他刚洗漱完毕,就见长乐宫的太监来报,说楚烈招来一批大臣去了湖边,楚桑直视着铜镜,心情渐沉至湖底,这低烧才退就把太医的话抛在脑后,病人哪有无法无天的权利——
“太医怎么说的?”
果然太监为难又道:“皇上执意要去……陈太医劝不住。”
他向来都知楚烈的固执,别说太医,就是他也拉停不住的,劝说也起不到很大的作用,明明是任性的那一方,还总能说出一堆堆看似理智的理由来,他反驳不了,只能要把青年那份自忽略的爱惜一并接手过来,除了他也没人多心疼青年一点了。
湖边亭外跪着好几个官员,楚桑现在只认得其中一人是礼部的侍郎,其他几人皆是生面孔,看脸色都已差极,还双手捧着什么东西,高高举着,像是要呈给青年看。
楚烈低烧褪了,神色也好了不少,黑发披在肩头,随意又洒脱的样子,略见削瘦的下巴还是很有傲据的味道。
只见青年向前倾了倾身子,把官员手中的卷轴接过,在手里玩绕了一圈,看也没看就甩在了跪着的官员身上,力道即狠又准,啪的声响脆生生传到他耳朵里,把耳膜都鼓动的生痛。
他停在湖中央的廊中,睁大眼睛看不远方的青年,低下的人都私传新皇暴戾酷杀,他怎么觉得就算使坏脾气的青年也是万分可爱的,至少比起躺在病榻上,能时时有脾气可发,也是大好事。
青年似笑非笑的脸如今现在有几分阴戾,也无损皇威,只是没有原来敏捷,过了好了会才察觉到他的视线,转头的一瞬眉头就松开。
“父皇,你来了?过来我这里。”
楚桑咳了一声,那卷轴无人敢捡,还散在官员身侧,露出一节上了色的女子裙摆,他撇开眼,“没事的话就让他们下去吧。”
青年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口气依旧刁难:“你们不是说还有事要禀告的吗,怎么不继续说了?”
带头的礼部尚书迟疑片刻,头磕在地上,答道:“微臣知罪,请皇上恕罪。”
楚烈握拳在嘴边,干咳了好几声,声音沙哑:“那你说说,是错在什么地方?”
“微臣不该自作主张,陛下既然说不立后那肯定是有陛下的思量,微臣斗胆妄揣圣意,罪该万死。”
他暗叹一口气,假装赏风赏花一样撇开头,不愧是混滑了的老油条,见风使舵使的比谁都快。
青年眼里有笑意,只是未达深处,“哦?不敢望揣圣意,可刚刚不是还揣的很起劲嘛,现在又不敢了?上朝时我说过的事,是不是还要再给你重复一次?”
“臣……不敢。”
楚桑单手一伸,按住青年的手,似安抚一样拍了拍:“让他们下去好了。”
那群人退下后,湖面都似宁静许多。
“是哪家的姑娘呢?”他忽然发问。
楚烈微微瞪大了眼,随即恼怒的看着他,黑瞳里似乎已经黑云压城了,“什么哪家姑娘?”
“就是刚刚他们给你看的……寡人只是问问,问问也不成吗?”
于公于私,于情于理,他也应该知道啊。
青年斜撑着下巴看着他,视线滚烫,像要从他眼里看出刚才那句话的真伪虚实。
他眨眨眼,坦然回视。
“父皇,你要是现在才说胆子小不敢跟我过,我是不会理你的。”青年捏着他手腕,凶起来的样子的确让人觉得很惊骇。
“什么……”什么叫胆子小,他都逆了天逆了祖宗了,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哪家的人都没有自家的好。”
青年皱着眉头扔下这句,就凑过来吻了他,唇舌间那股参药味实在难闻,可是青年的热情又让他万分着迷,温柔又怜惜的动作,好像他真的是什么人间没有需要好生珍惜的宝贝。
“现在后悔是不行的。”楚烈从上看着他,不知怎么的,就显得有些急切脆弱,“我已经那么努力了,父皇。”
“…………”
“我们不欠这个国家什么了,我做的足够弥补我们两的事,我还的干净,一点也不欠了。”
只是喜欢而已,其实也不是什么杀人放火的事,但就是像欠了债,良心有愧一样。
楚烈平日不说,但不代表心里不明白。
大家都在弥补过错,只是各有各的方式罢了,楚桑不觉间就觉得透不过气,平复着心情,嗯了声,“是不欠什么了,我们还干净就好。”
楚烈舒了口气,眉眼都舒展了。
“反正以后也不是我们的时代,百年后不会再有人知道我们,遗臭千年也无所谓,反正都成了黄土,谁听得到,咳,寡人其实偷看过史官写的起居注,其实再臭一点也无所谓了。”
他年轻时也做过许多错事,都清清楚楚的写在那本册子上,以后的人都瞧得见他们的过错,或者那么点点功绩,除此之外,他们的名字只是几点笔墨的价值而已。
楚烈听到这番外,显然很高兴,一时兴奋就咳嗽了起来,最后脸都咳红了,他手忙脚乱的给青年拍后背,不留情面的斥责:“呆在房里不是好好的,出来吹什么风,小心被风吹走了。”
“又不是什么大病,调养就好了,父皇你慌什么。”
“谁说不是大病……”他猛然住口,尴尬一转:“就是小病也不能大意,不听太医说的话总会吃亏。”
影子倒在湖中,波光粼粼,两人就似融合在一起了。
楚烈赖在他肩膀上,蹭了几下,含含糊糊道:“父皇,那个李修尘好像是风寒湿邪后喘病复发而死的。”
“你去查这些做什么?”他沉默下来,反握青年手臂用力一扯,把两人距离更拉近了些:“是闲的没事做了?”
“父皇以前不也查过吗,还查的比我透彻多了。”青年微笑道,神色轻松。
“他死法如何管我们什么事。”楚桑气得脸发红,手指戳住青年的脸:“你是不是存心让寡人不愉快?我们过我们的日子关一个死人什么事。”
楚烈的脸给他戳得有些红,抿着嘴垂着眼的样子很有点黯淡:“是,是我乱想了,我近来头乱的很。”
他也察觉到青年近来变幻无常和易动怒的性子,病痛似乎削薄了楚烈一向引以为豪的忍耐力,他无可奈何的苦笑了一下,只是紧紧抓着青年瘦了许多的手臂,楚烈蹲下来,从湖边捡起一块小石头,发泄一样扔了出去。
湖面开出一串漂亮的水漂,只是把影子打散了,碎影和湖边的树影扭曲在一起,倒是热闹。
楚烈抱着他,阴霾也随着水花平静散去,笑道:“如果我以后犯傻,父皇你就拍醒我好了。”
其实他们都在一起犯傻,但光是一想到要把对方分一块出去,就难受的要命,傻子总是快乐过贤者的,于是两月后,楚烈在宗族里挑了一位稳重的少年,打算立为太子。
虽然都是楚姓人,但实际上已经不一样了。
楚烈在挑中人的那天露出了一副尘埃落定的放心的表情,酒喝多了后就一直趴在他身上说了很多话,大多是无关痛痒的小事,和酒气混一起,让他觉得很轻松愉悦。
毕竟他们因为私利而牺牲了那么多。
越是想把对方抓牢一点,越是觉得沙子从指缝里不停的漏着,越紧越漏,简直像在嘲讽他的无能一样,世事总是求而不得,得而不珍,欲珍却晚,可楚桑只要一想到时候青年必须一个人独活时的场景,就觉得不可以忍受,他已经不年轻了,陪不了楚烈多久的,就这样抱着对方,还是感觉时间在腐蚀着他,不真切的像一场黄粱一梦,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或者清醒。
是不是每对相爱着的人都会像他这样患得患失呢,如果只是长辈的话,就根本不需要这么心烦,或许还会比现在更长久一些。
半睡半醒间,在安静的房间里,他仿佛听到楚烈的声音,楚桑忽然清醒的从床上坐了起来,没有任何人在说话,青年还侧躺在他身边,呼吸绵长。
没来由的胸口一热,找不到一点理由,他摸了摸青年的脸,拨开额前散着的黑发。
“皇儿?”
大病过后的人还睡得很沉。
“烈儿?”他不死心的低头,额头相抵,又叫了声。
青年长睫毛似乎颤了一下,像是在挣扎该不该睁开眼。
“楚烈。”
楚桑没有再继续叫下去,其实刚才的冲动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他只是想起很久之前,摄政王手把手教过他写过的一句诗。
无论去与往,俱是梦中人。
隔了那么悠久的岁月,孩童时候学过的,几近遗忘的诗才忽然入梦,打得他猛然惊醒。
所幸的是,楚烈还在他身边,只需要再叫大声一点就可以叫醒,无需等待。
这天晚上,他做了个长达万里的梦,那时候他们都已经老了,路上依旧没有驿站,他和孩子还在寻着家。
番外:
元庆十二年,二十一日,帝卒于长乐宫,遗诏以皇父楚桑嗣皇帝位。二十五日,皇父楚桑重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安庆元年。
番外:
元庆十一年,酝酿许久的新官吏制在全国全面铺开施行,这也正好是容愈为相的第十个年头。
有些地方显然不愿意接受新的审查机制,为了平息荆州的暴乱,容愈只好亲自前往压制,就算那么多年过去,他还是对楚烈过于铁血的手段颇有微词,特别是近几年,皇帝的脾气似乎越发的难以琢磨,在朝堂上的喜怒无常也让大臣们伤透了脑筋,幸好皇帝虽严苛,但不滥杀无辜,他已觉大幸。
太过霸道的人多少都会有些自负,这点认知容愈在皇帝身上感受的淋漓尽致。
本来计划中他可以在皇帝三十寿辰时赶回来的,无奈路途遥远,又遭遇大雨,等回京时寿宴早已过去大半个月了。
这晚他处理完公务冲冲回府时,在书房里见到一个不速之客,外头正下著雨,风声拍打着窗,来人袍子未湿,看来已等了好一会了。
“张公公。”他朝来人点了点头。
火盆里炭火烧得正旺,屋内的温度有些热的过头了,容愈解下披风,端起茶看着面前的人。
张丘是近几年里皇帝身边最能干受宠的心腹,平日也是一副深藏不漏处事不惊的模样,今日却脸色苍白,神态飘虚。
“容相,皇上有请。”末了,又补充道:“还请容相换衣。”
他此时穿着一品官袍,若是换衣,那就代表这是密传,容愈沉思片刻,掩下眸中暗沉:“好,请张公公稍等片刻。”
外头风雨不停,枝叶凋残,一副萧肃相。
虽然早已贵为宰相,他的府邸却和当初的尚书府差不了多少,依旧人丁稀少,容愈没有纳妾,更没有娶妻,来说亲的自然是多,他都一一婉拒。
人在朝中,恰如身在漩涡之间,稍有行差踏错则尸骨无存,越是爬的高,到时候跟头就会栽的越痛,自己一人也就算了,若有家室,岂不是连累。
他还记得当初自己父亲倒台后府上的凄凉惨状,不是每一个被卖到小倌馆的落难少爷,都会像他一样那么好运气,遇到贵人,救他一世。
一个人就已经很好了,了无牵挂,只要想着再为国家多做点事,人生就已经很圆满。
可显然楚烈不会这么想,他其实也想得通,楚烈是天之娇子,一出生就是太子,注定的国君,人又有手段,什么可以拿捏的住,这种人,只会想要的更多,更多,对想要的事也好,人也好,总是要不折手段的留住。
他也有想留住的人,可终究还是不敢,理智让他及早抽了身,不是所有人,都有像楚烈这样不怕死的固执。
“来了?坐。”
皇帝侧躺在龙榻上,阖眼修养着,倔强紧绷的下巴和一直在敲打着的手指泄露出些许的心烦,男人不耐烦的掀开眼皮,吩咐他坐下后,又咳了几声,“荆州若还在闹的话,就暗地里带些兵过去就好,面子功夫你也做足了。”
他早已预料到楚烈会这么做,颔首道:“是,微臣明白。”
男人嘴角一弯,英俊的脸就带上了点嘲讽:“容愈,你这哪是明白。”
就像他永远对楚烈都有莫名的微词一样,男人对他也从没放过真心。
虽然他们君臣关系已经十一年了。
男人摆摆手,无奈似的,撑着自己额头叹了口气,不知怎么的,就让容愈觉得有些尴尬,他看惯了楚烈的强悍和暴戾,这么忽如而来的软弱真让他无法适应,好像偷瞧到别人一直藏掩着的隐私。
“张丘,把诏书给他。”
容愈不明所以的看着太监从柜里拿出一卷圣旨,他捧在手里,男人没发话,他也不能随便打开。
男人神态平静,语气也很平静,除了眼里微浑,一切都看不出异样,“打开,看仔细了。”
容愈一目十行的读完后,手心不觉间出满了冷汗,只是表情还是常年的淡漠,无甚起伏:“争议太大,微臣还是觉得……不妥。”
男人看着床幔,那副表情就和以前弹指间夺人生死,下屠城令时一样,不会因为外界的意见而改变想法,皇家人任性似的傲慢:“我觉得很好,再好不过,容愈,我可以相信你吗?”
不行,没这种做法的,除了前朝一次荒唐的篡位,史上还未出过……这等事。
容愈握紧了这卷诏书,喘不过气一般,肩头生疼,“臣明白了。”
男人似乎舒了口气,年少时眼里常见的戾气已经单薄了许多,锐利也好,冷淡也罢,都沉在眼里,浮不上来了。
“我近来身体不好。”楚烈没看他,只是自顾自道:“有些打算,总是要提早做了的好,免得以后手忙脚乱。”
所以说……太多的牵挂,不是好事,容愈轻声回应:“皇上说的有理。”
楚烈置若罔闻,像是在回忆什么特别满足的事,“我这一辈子,老天待我已经够厚,该有的都有了,本不该有的,我也有了,其实也没什么好争的。”
“…………”
“对了,容愈,你这个年纪还不成亲,我一直很好奇这是为了什么。”
他被这句话问的昏头转向,直言:“臣不想牵连太多。”
男人一愣,随即大笑,“牵连,容愈,你胆子也过小了点吧。”
容愈默然不语,不是他胆子小,而是童年时代的家变就是一场驱散不去的噩梦,时时刻刻提醒着自己,与其如此,不如不触景伤情,图个自在清净。
“能让什么人牵连着,即是大幸,也是不幸啊。”笑罢,楚烈又干咳了好几声,露出异样的神采,眉眼都温柔几分:“原来如此,你是怕牵连,我父皇还猜测过你是不是有难言之隐呢。”
容愈一怔,随即明白过来,耳朵微微发烫。
“下去吧,这旨今天就交给你了。”
他胸口里放着这道要命的圣旨,就像千斤大石压迫着自己一样,容愈走了几步,忍不住回头一看,太监已经放下床幔,点起安神的药香,透过那些繁复锦丽的床幔,他看不真切里面的人。
踏出长乐宫的时候,惊飞雷雨依旧,刮得他两眼发湿,根本睁不开。
“爱卿?”
“爱卿,回神了。”
容愈猛然一惊,身子坐正,此时暖香阵阵,棋盘上错落着黑白棋子,哪有什么风雨雷电,他盯住心神,将手中持着的棋子摆入棋盘。
“臣走神了。”虽然早过了而立之年,他在这个人面前总有种没法褪去的羞涩。
“无妨,无妨,寡人也知你事务繁忙,陪寡人下棋真是难为你了。”
容愈笑笑,道:“是皇上不嫌弃臣棋艺差。”
皇上棋艺精湛,就是速度慢了些,现在天气暖和,正是春意正浓的时候,就容易打瞌睡,有时皇上捏着一枚棋子都可以眯着眼发呆许久,过一炷香才恍然回神。
陛下靠在软榻上,整个人都陷在松软的锦织靠背里,眼皮半搭耸,有点懒洋洋的模样,样子还是他所熟悉的清俊高华,与记忆里似乎相差无几。
“爱卿,若你还是走神,就别怪寡人将军了。”
“是。”容愈合拢心神,鼻尖被暖香搔的□,在这种怡人的环境里,连他也有点乐不思蜀了。
不知道是不是公事太多,容愈最近越发觉得力不从心,一日忙完后独自躺在床上,就现在茫茫然起来,真真怪了。
陛下棋子走势看着温和,实则凶辣,容愈不敢掉以轻心,全力部署。
有太监上来呈报:“皇上,太子求见。”
他看到陛下把棋子捏进手心里,背脊微微从靠背里直了起来。
没一会,远处尽头繁花处就有一抹玄黑身影,隐隐龙纹,正是当朝太子朝服,那抹身影穿过多事的春风,踏过繁花似锦,衣袍都在春风里微微扬着。
容愈起身,规矩有礼拜见道:“参见太子殿下。”
年轻太子眉目尚算的英武端正,面相一派温和沉稳,扶起容愈,谦和道:“太傅请起。”
陛下还阖着眼,手搭在软榻的把手上,寡淡着脸,像所有长辈一样关心后辈的学业:“最近在礼部有学到什么?给寡人说来听听。”
容愈也在一旁听着,陛下也会适时给出一些反映,让年轻人继续有勇气说下去,他作为太子现在的太傅,也自是希望年轻人能够让陛下宽心点。
先皇的那一笔,画得够浓够艳,像楚烈这种皇帝,一个就足够了。
也许以后庆会出现更优秀的皇帝,可对陛下来说,这也没什么意义了。
“很好,以后容相对你的教诲,一定要好好记住,下去吧。”
太子跪拜,脸有喜色:“谢父皇,儿臣告退。”
他瞧见陛下手顿了顿,像难以忍受似的侧了侧身子,隐着眉间的不耐烦:“别叫我父皇。”
话虽不大,足以让年轻人脸色煞白。
太子退下后,棋局继续,容愈等着对方下子,只是许久过去,陛下闭着眼后似是没了动静。
容愈耐心等着,好一会后,才轻声唤了声:“陛下?”
真是睡着了,身旁的宫女们适时拿来毛毯,悄悄盖在陛下腿上,容愈悄然起身,将边角拢好,把陛下手指间夹着的白子给慢慢抽出来。
猛然抬头间,隔着非常近的距离,他发现陛下发间暗藏着一抹灰白,容愈徒然垂眼,难以忍受似的看着自己手中的白子,眼眶酸痛非常,胸腔发疼,差点就把持不住了。
原来,记忆里那个会拿扇子拍他头的青年已经不在了。
“陛下。”容愈跪在榻边,仓惶掩着自己的脸,生怕让人看到他眼里控制不出的泪。
他这辈子最感恩的人,原来也已经老了。
“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