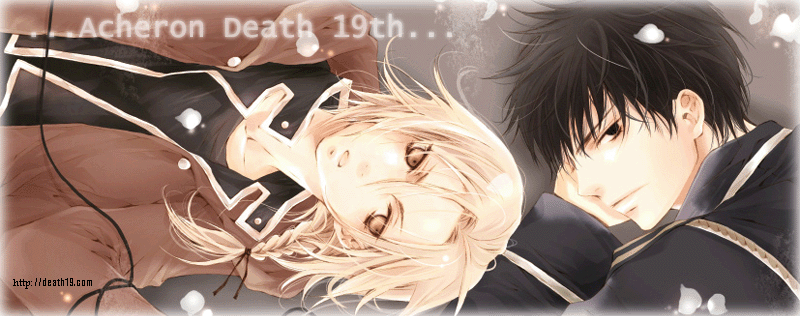行越国诏之番外2 路边桑莫采
又是茜花雨汛,花期到,桑丘的茜花四处开放,点缀得山野间青白粉红一片,依碧晴山傍荀溪的那处山脚,建起一座行宫,行越太主父就居於此地,本来这是件大事,但事实却是──太主父到底是否在这里都很少有人搞得清。乡间人淳朴,对他们来说每日将田地耕好,是真正要紧的事情。
溪边有一人,穿青布小衫,前摆只到膝盖,这款式最最凉爽轻便,他似想去水中沐浴。村中几个少妇洗衣正经过,看到这人立刻停步。
“谁家儿郎?”
“许是主人家?”
“是了是了,定是主人家,赵氏的子弟,才能如此好人品呢……”
少妇们议论纷纷。
那人远远招手道:“大嫂们来洗衣服的?这里水缓!”
少妇们笑作一团,越地民风开放,她们听这小哥儿如此说就走上前去。走近瞧这人,果真是个美男子!青色短衫遮不住春光,胳膊和腿虽然不如农家汉魁梧粗壮,恰骨肉均匀,十分可意……她们如何见过如此俊的人品?
一个妇人道:“小哥儿不是这里人?”开口的少妇嘴角一颗美人痣,大眼睛,眉目间颇有风流之态。其他女子见她如此,知道她有心勾缠,但见这人也有意,心道若是主人家的人,这干女子自是随他的欢喜了,便也坦然。
男子道:“不……”
“还以为小哥儿是赵家的……”
男子心道:这里的村庄都是赵氏的地。想罢狡黠的一笑道:“我是赵家的子弟,不过刚游学回乡。”
少妇见他气度如玉,认定是主人家子弟,媚眼道:“哥儿要不要四处转转?看那边桑田,可茂盛得很!”其他女子识趣地纷纷道:“那我们先走,衣服还未洗……”一转眼散光了。
男子本有些犹豫,心想自己溜出来已经不对,如果再做什麽事,被那人知道岂不要死?
可转头看这村妇眼神可人,胸脯贴著他的手臂,许久未曾尝到肉味……於是神色轻佻道:“正好,大嫂带路?”
桑田中有块晒桑叶的平地,放著竹幂和斗笠,四面密不见风,桑叶茂密如同帐幕。
男子尴尬:“在这里?”少妇笑著扑到男子怀里:“好哥儿,难道不知幕天席地才有味儿?”说著拉男子的衣襟,男子白皙的胸膛袒露大半,两人情热,刚躺下,不知道哪里的响动。突然桑叶丛一分,有人闯过来。
两人赶紧分开,村女抬头吓了一跳。
来人非只一个,竟是一群,为首的那人她熟悉。正是这里主人家。
他那几十随从有的跟在身边,有的站在田边看热闹,都觉得十分新奇。
赵家的这位家主三十出头,刚毅英俊的面目,平时十分可亲,现在却狰狞,仿佛怒到极处。他冷冷瞥一眼跪地的村妇,沈声道:“起来,滚!”
女子见主人脸色,仓皇跑开,瞬间就无人影了。
美男子也往後退,却听赵家家主牙缝中崩出字:“你敢走?”
赵无恤眼前这位美男子,正是行越前国君,如今的“太主父”,吕赢拉上自己不整的衣服,跟他交换眼色,只怕揭穿自己的微服,在从人面前丢脸。
他装模作样道:“这位大人,您有何贵干?”
赵无恤瞪他,如何不知道他心思,切齿道:“桑丘民风浮浪,让客官见笑了!”
其话中之怨毒,让吕赢背上生寒,他陪笑道:“这,主人家……不要怨恨。那是你村中女子吧?我只是闹著玩罢了!”
赵无恤阴沈道:“做主人的,原不该阻挠您的兴致!”
吕赢咳嗽道:“那我先走一步……我只是路过而已。”
“都给退出去,一里外等我!”赵无恤对他手下从人说道。其中几个有身份的总管,依稀认得吕赢,憋著笑应道:是!
他们退得快,更退得干净干脆。吕赢目送这群人走,回头问:“你不是去朱秋家了麽?”
赵无恤见他毫无愧疚之意,反端起架子搪塞,著实怒了,冷冷道:“你便只想说这些?“
吕赢怎听不懂他意思,心想:这人登堂入室是真,可我堂堂贵胄,难道连女子也碰不得?被捉到当场,更加羞愧,事关尊严,他嘴硬道:“便是这些,再会!”理理衣衫,抬脚便走,没走出一步,就被拦腰搂住。
“赵无恤!你干什麽!”
那人不回答,径直将他扛进田里,桑树低矮,不太合用,无妨,他扯下那人腰带,并起双腕,择一根粗壮树枝绑了。
吕赢腰带一扯,那简陋两块布下,满眼春光撒得不剩下什麽。
光天化日,吕赢如何经得住这个羞辱?急叫:“赵无恤!”
他面色通红,浑身发抖,不知是怒是羞,紧夹要害的修长双腿,刚起了一点就被打断兴头的分身,尽数在赵无恤眼底。赵无恤本是发狠吓他一吓,没料能见识这等风情。一时愣怔。
这人少年跳脱,年纪渐长,比从前懂掩饰,只要不说话,君主威仪凛不可犯。他看惯他华服高冠的样子,而今在这野地,身无长物,粗布衣衫凌乱,带著三分可怜……自是叫人情为之夺。
吕赢兀自瞪眼质问:“你要如何?赵无恤!这是外头,与其废话不如快放开我……”
不提还罢,赵无恤只恨他轻浮,竟在乡间野地与妇人苟且,冷笑道:“明明喜欢幕天席地……怎说不要?”说罢吻上,吕赢如何肯依从,扭动抗拒,忽闻撕拉一声,青布薄衫应声碎裂,片片扯得离体。大手越发放肆,上下游移,吕赢刚刚被逗弄得情起,如今更受不住,他十分窘迫:“……赵无恤……你别……”
雨讯天阴,有雾气潮露,层叠的桑叶之上,天光朦胧之下,黑色长发纠缠在手臂,略嫌白皙的男子身躯刚柔并济,仿佛上好玉石雕琢,山泉涤洗而成,他身下的叶有绒毛,弄得他很痒,於是肆意扭动挣扎,紧崩的小腹上汗水晶莹,半暗半闪。
“别动!”赵无恤气息急促起来。他定定心神,忽然邪笑,言道:“你知道麽?百里村中都是未脱籍的奴儿,身为家主我可生杀予夺,律法许可,天经地义……即使游民犯奸盗在此地,家主也可随意处置!”他说罢,居高临下,攥起他汗津津的下颌,抚摩过脖颈,胸膛不见胭脂色的痣,而有两点细小胭脂果挺著,伸指夹住,软绵绵仿佛能滴出汁液来。吕赢吃痛,颤声问:“你要怎样?”
赵无恤看他一眼,吕赢背上寒毛直竖,他不曾见他如此邪恶神色,
“你与那妇人在这里欢好……很过瘾麽?你犯奸被捉,自然要处置!”想到那场面,赵无恤怒意更盛,他猛地分开那人紧张闭合的股间,手掌在臀上肆意揉搓。
“放开我……不可!”吕赢苦在手还绑在树干上,无论怎麽也抗拒不了,只能眼看他以如此猥亵的动作戏弄,吕赢怕这人现在发情,这是路边,万一有人经过了如何收场才好?那一堆从人也不知道走远了否?
他心里一急,眼底发红,就想哭出来。
赵无恤知他怕了,俯身,吸他的舌尖,细嫩唇瓣被啮咬,如要揉碎。他强将他摆得趴伏於地,吕赢双股战战,几乎跪不稳,然而这时瘫软却将著紧处蹭到毛茸茸一堆叶子上,更是难受……吕赢哀声道:“赵无恤……你不要如此作弄!”
将他长发抓在手中,慢慢楸紧,吕赢吃痛,只有仰起头,柔韧的腰线如弯弓曲折,透明的汗水滑过脊背,淌进那双瓣之间,这人年纪长了,身体竟还若少年时那样涩嫩。
赵无恤露出白牙,面色阴森,低低笑道:“你是犯了奸,也是我家中人,自然归我处置……还有人会管不成?谁又有胆子管!”赵无恤居高临下,语调中满是霸道专横的味道,变了个人似的。他的手慢慢滑入吕赢两腿间的阴影处,不等他夹遮,就握牢了,细细调弄,吕赢的分身比例匀称,形态甚美,握於手中渐膨起时,有汁液泌出,如握著一只饱满果实。
不多时,揉捏滑腻嘶嘶有声。
头顶上晴空空阔,田中四面透风,细微声音传出去,可传得老远,吕赢不敢大声求饶,更不敢大声呻吟。
“赵……这里怎麽能……你不要……”吕赢只顾求饶。
“既然你犯了奸……自然生死随我处置……”
吕赢惊惧羞惭中,知他强词夺理,却也无法可想,他想发泄,苦於被握得太紧,不敢扭动又不敢抽身,真是不上不下,忍不住道:“赵无恤,你……你待如何,才……不生气了!”
“主人之命不听?还敢直呼姓名……”赵无恤舔过他肩头汗珠,咬下去,一个牙印,“……胆子不小!看来罚得不够!”赵无恤手中加重力道。指头抵在细小穴口慢慢润渍,渐抵入去。
“赵……”吕赢刚开口
“叫我什麽?不学乖麽……” 手指已经拨开那处。
吕赢浑身一抖:“不!”这样浑身裸著,双手被缚,要害如同玩具被握著,说不出的羞耻下流,他将头埋下委屈道:“我……我知错了……再也不敢……”
“文不对题,要罚!”邪恶声音丝毫不通融。
吕赢终於知道必须陪他发疯癫,没奈何,委屈地道:“主……家主……大人……奴儿错了……”
赵无恤道:“错在哪里?”
“不该……不该招惹……”
“为什麽不该招惹!”
“因为……因为……”吕赢的手无力支持,要倒下去,赵无恤伸手,将他拥入怀里。
“说……”他在他耳边劝诱道。
吕赢不甘心,却又怕招来什麽毒损招数,他道:“……只有你……可以……”
“可以如何?”
“对我……”吕赢脸已经烧得如炭火一般,再也说不下去了。说这样荒唐的话,真正羞到极处,让他四肢无力,在这人臂膀间挂著动弹不得,吕赢刚才那席话出口,一瞬间真觉得自己是那卑微奴儿,於田中被无辜捉住,主人家蛮横下流,可却无人来救……转头看,一双眼炯炯看他,满是情欲,如欲择人吞咬。他怯道: “你满意了,那就……”
绑得发麻的手终於被解开,吕赢已没有力气挣扎,任由那人抱他坐跨在膝上,赤裸胸膛对著那人面孔,呼吸犹如抚触,徘徊前胸,让敏感的果实更加挺立。这太过丢脸,吕赢闭眼不去看,
青涩味道弥漫开来。
吕赢看不到,却知道是揉碎的桑叶,不容他多想,更不容他拒绝,汁液揉进他双股间,手指勾缠肉壁,淫糜的声音响起,折磨许久,手指探入得深了,那人扣住了不让他躲,终於,赵无恤亦将衣衫半褪,他的分身抵在那处。他抱著他,圈著他,扣著他汗湿的颤抖的细腰,抚摩他已经发红的臀瓣,後头那巨物分开密口,缓慢抵进深处去。他不许他逃离身下惩罚,因著姿势,实在探入极深,从所未有,吕赢只觉得害怕疼痛如要涨裂,扭动道:“无恤,不要再深……你要弄死我……” 他如此口不择言,引得那人更狂邪的狎弄,双手挤得他夹紧那处火烫,越发的著紧摩擦,他越是要躲,越躲不去,抽身时,那人如影随形,力气用尽落回原地,却难以借力被捣入更深,一阵眩晕,他周身围绕那火烫的躯体,那人臂膀贲张,撼摇不动,崩得紧紧那脊背,绢布亵衣全都揉皱了。吕赢只觉得起伏间电光石火,如登仙,又入黄泉,他克制不住,再也呻吟不停,哪里记得著这是桑田畔大路边。
……事毕,赵无恤见他手腕的淤痕,和那胸前点点狼籍,也觉得自己做的过分了。
吕赢力气耗尽,半梦半醒,迷糊地躺在他怀里,被他包在衣服中,可惜修长身体遮不完全,依然露出些许春光,他轻唤:“吕赢……外头湿,回去再睡!”
吕赢尚在梦中,梦里春梦,十分不巧是那多年前御花园百花丛中,他与美人欢乐颠倒时,忽然闯来一个少年将军,那少年伟岸英挺,目光炯炯,搅得他心烦意乱。
吕赢蹙眉喃喃道:“我自与美人好,你……别吵……”
赵无恤脸色顿时发青,咬牙:“那现在且睡罢,回去,就不用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