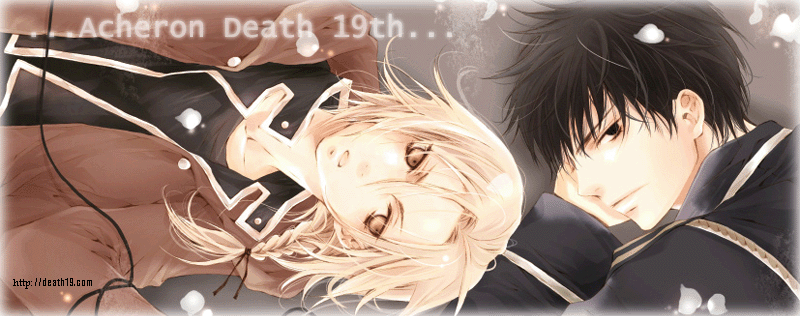番外一 程沐 顾珽
冬日的宏国都城,早已经被纷纷扬扬的大雪覆盖成了一片素白。
雪霁之后,日光随意铺洒其上,映出明晃晃的光芒,竟有些刺眼。
虽是如此,依然有小片的雪花零星落下,程沐搂着一堆卷籍,艰难地撑伞走上了高台。舒展如凤翼的屋檐下,早有宫侍们替他将伞收了,又恭敬地挪到一边去;又有一个小侍垂首挪着小步,进门通禀——程沐立在门外,已然听见屋内传出软软的童稚声,仿佛清澈的流水浪花。
程沐兀自笑了笑,小侍冲他施了礼,示意他进去。
屋内,熏炉正氤氲地吐着一丝热气,缭绕在那铜炉的错落山峦装饰上,恍若海上蓬莱。
一位大约七八岁的孩童披一领光滑的锦缎白氅,举着两截青木香好奇地往那熏炉上戳去,谁想腕子被那铜炉一烫,顿时失了手中的香木,后退几步道:“先生……”
那屋子的窗下,摆着一张巨大的书案,上面井井有条地码着成摞的书卷。书案后,男子正蹙着眉头对孩童低叱道:“阿白,你将《礼记》誊写完了?谁又许你动那博山炉的?”
被唤作“阿白”的孩童一怔,满腹委屈地垂下头去,揉一揉被烫得发红的手腕,又噙着泪偷觑了门口的程沐一眼,悄悄地窝到了屋角的小案旁。
“见过时先生。”程沐微笑着对男子——秘书监时耘施礼道,“这些书卷太子已经阅毕,因此命我来还,又写了张书笺,还望时先生帮忙取书。”说罢,将那写书卷搁在书案旁的小毯上。
时耘起身接过书笺,又伸手挪过不远处的连纹坐毯,笑道:“大雪初霁,然润前来着实辛苦了。烦请暂歇片刻,待我取书来。”便欣然往屋子的另一头走去——那里镂了一道门,直通那陈了数不清的书架的屋子——宏国历来最珍贵要紧的书卷,都被收藏在这里。
程沐点了点头,在那厚实柔软的毯上坐了,瞥了一眼书案上还饱蘸着浓墨的毛笔和那方流水纹的砚台,目光最终落到了屋角的孩童身上。
那孩子似乎也觉察到程沐的眼神,抬起头蓦地冲程沐咧嘴一笑,露出了两排碎玉一般的牙齿。程沐一时想不起这是哪一家的公子,但断然肯定并非时耘之子,惶惑之下也只能对孩童笑一笑。
“你是程洗马对么?我见过你的,在上次陛下的私宴上。”孩童再次笑着,颇为自信地说道。
程沐不免有些好奇:“小公子是……”
孩童才要开口,却被人打断:“阿白!”程沐循声望去,但见时耘立在门边,手里捧着一摞书卷。
孩童畏缩地瞥了瞥时耘,连忙再次拾起毛笔抄写,黑漆漆的墨汁沾在袖口上,开了一朵小小的花。
“这……”程沐歉然地笑了笑,不知该如何说话。
时耘似乎看穿了程沐的心事,笑道:“这位是刘道之刘侍中之子刘素,小名阿白。刘侍中常随陛下左右,唱和赋诗,有时也带着阿白。只是他唯恐因此贻误了阿白读书习字,故特向陛下求了,让阿白在这里跟着我誊些儒家经典,偶尔读些道之类。”
程沐这才想起,前日陛下的私宴中,他随侍太子身边,的确在纷扰人群中瞥见过这个小小的身影——原来竟是刘道之的孩子,再一细看,刘素眉眼之间当真有乃父的清雅气韵。况且自己也曾听太子顾珽说过,刘道之与时耘私交甚笃,如今见时耘对那刘素的严苛态度,果然所言非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