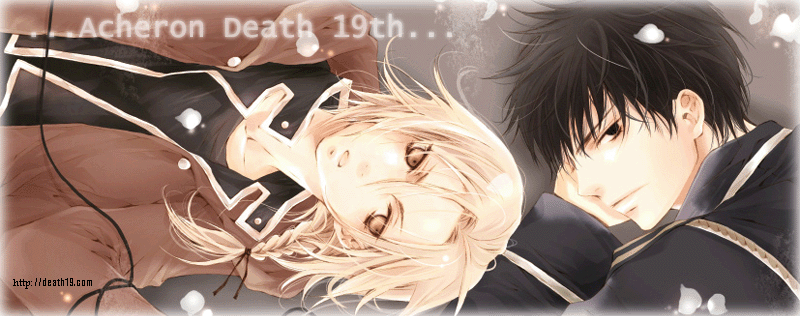改不了字体, 抱歉不知道咋回事
番外 落香尘
程凤常头一次见着苏鹤姿,正是三秋时节处暑天气。
是日天朗气清,云淡风和,独有辣刮刮的太阳晒得人眼晕,苏州城外官道边的那棵老柳上趴着只晚蝉,有气无力地鸣着声响。
程凤常立在树下一阵好等,直等出一额心焦焦的热汗来。
眼看着日头都有些斜了,站在后首的通判忍不住开了口,刚喊了句“大人”,便瞧见程凤常不耐烦地挥挥手,一时间只好把话头生生咬断在嘴里,心中更是憋闷。
程凤常看了一眼远处的官道,依旧是浓青的树影夹着灰黄的地面,半点不见车骑驰来那种尘土喧天马蹄翻滚的架势,顿时觉得这清清净净的官道……清净得让人有些恼火。暗地里,心头不由得冷笑一声:“这位巡盐御史苏大人……真是摆得好大的架子!”
待得日头毒得连蝉儿都鸣不动时,苏州城门边痴痴苦等的一干大小官员终于起了一阵小小的骚乱。
程凤常仍旧维持着一贯那把淡淡的语气朝畏畏缩缩来报信的差役问了句:“苏大人已经到了?”
差役小心觑一眼他的脸色,虽未黑如墨斗,却也不太好看,只敢虚虚应了是。犹疑片刻,又小声补了句:“苏大人说江南风光定是离不了水的,水路景色才是绝品,故执意乘船……”
程凤常“嗯”地应了一声,过得片刻,忽然又添了句:“知道了。”
苏州府大小官员枉杵在道儿旁枯守了半日,而今御史大人竟已先行走水路入了城。出城迎候的俏媚眼儿无端端抛给了瞎子看,饶是官大一级压死人,那被压的几位大人们仍是气得胡须乱颤手脚发抖,无奈敢怒不敢言,满腔的怨气尽皆撒给老天,只不住跺脚跳骂:“这鬼天气,真要热死人!”
待骂了几句,扭头见得这一府之长程凤常面色如常不言不语,又蔫蔫住了嘴,心中暗叹知府大人端得是修养绝佳气度过人。
等愣上一头再抬眼,已见程凤常衣带清风袖翻云朵迆迆然迈步走了。
通判疾步撵上去,刚一张嘴,程凤常已答了他句“回府”,彷如今日笃定了不叫他说句囵囤话一般。
通判缩了缩肩膀,心道原来知府大人也窝了一肚子火气。
程凤常确实是窝着一肚子火气,若论品阶,他是比苏鹤姿高上一品,但阖朝皆知苏鹤姿是太子近臣,端个架子原也无可厚非,而今看来,此人……却是太过狂妄了。
只是他狂他的,程凤常不动声色地笑了笑,这两淮的泼天富贵与无际风月,难道还淹不没几分狂妄么?且看他能狂到几时罢了,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高楼塌,亦是别有一番趣味的。
自偏门进了府,他也未往正厅去,只在浓翠的树荫下站了一站,又朝西院的小室走去。
程凤常此人,不嗜酒馔,不溺女色,不耽诗书,不爱银钱,仿佛是为着寻求灵魂本真的苦僧,已将肉身的欲望一股脑抛弃了,连喜怒哀乐都不尽明显。做官做到这个份上,硬生生叫两淮那泼天富贵与无际风月也寻不得个缝隙来浸染他,是以这苏州知府,一做便是三年又五载,到而今,已是第九个年头。
他惟独有一个嗜好,便是制伞。
谁也不知他从何处学得这制伞的手艺,反正他就那么会了,也就那么制起伞来。
程凤常制伞毫不讲究,柄骨取的是西院墙根角的几櫕竹子,也不论紫竹翠竹湘妃竹,哪株不幸入了眼就是哪株,伞面的棉纸是在离程府最近的那家书斋里几文钱一打买的,便连刷的油也是秋收时自制的柿水。
伞制成后,也不曾赠送亲友,也不曾入市贩售,更不曾于烟雨霏霏时分撑着去沧浪亭畔寒山寺边走上一遭,就那么往晒架上一悬,经了风,着了雨,积了灰,便连着尚未滚落的水珠灰尘一道往薪火堆里一扔。
不吝不惜,毫不在意。
沾了水的竹柄在火舌里炸得噼啪作响,程凤常就站在火堆边哑笑,如此你你我我地付之一炬,同归于尽,有什么恩怨也作了尘土,皆散了。
程凤常制的伞,惟独讲究的是伞上绘的图样。
许是因为出身世家,他的书画都十分出挑,一枝花,一泓水,一捧月光,都绘得灵性逼人。
程凤常无声无息地进了西院,又接着制他的伞,到月上树头的时分才歇了手。
半庭空明的月色映透地堂,衬得新伞上的图样笔意灵活,墨姿萧索,正是长风荡清天地后,浩浩江水边一树凋零的梧桐。
程凤常搁下笔,眯着眼盯着半干的伞面看了一忽儿,又提笔在旁边题了一行小字。
西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
待心满意足地拿着伞推门出去,举目正见凉沁沁的月光下立着个穿宽身白袍的人,手中提着一盏闪烁不定的灯。程凤常吓得一退,半边身子又退进小室里。
苏鹤姿见程凤常虚倚着门框,半边脸叫浓重的阴影埋了,露在亮处的半边脸便生得格外细致,那眉那眼,连拿在他手里那伞面上描的苍黄梧桐也及他不上,由不得便抿着唇角一笑。
他这一笑,整张脸孔便生动起来。因为鼻梁特别挺,人中特别深,嘴唇特别薄,又时时有意无意地勾起一边嘴角,玉般的面堂上,眉眼间夹着点漆般的眸子,左颊的颧骨后面还闲闲地生了颗小黑痣,月下瞧来,平白地少了几分人气。
程凤常一时半刻吃不准这是哪一路妖魔,索性不问不动,只同他枯耗着。
苏鹤姿也不着急,肆意地盯着程凤常看了半晌才慢条斯理地开腔:“程大人,下官苏鹤姿”,话一出口,倒是自己也禁不住笑了,“……特来拜访。”
程凤常啼笑皆非,别过身子从小室里走出来。
“程大人专注,可教下官好等”,苏鹤姿似笑非笑地微扬一扬下巴,无意间扬成了一段俾睨众生的姿态。
“彼此彼此”,程凤常淡淡扫他一眼,“……苏大人。”
他这一声不咸不淡的“苏大人”,竟叫得苏鹤姿浑身轻轻打了个抖。
却说程凤常这是头一次见着苏鹤姿,苏鹤姿却不是头一次见着程凤常。
那日正是新榜状元郎巡街,苏鹤姿与一干同僚坐在酒楼的窗边,远远一照面,瞧见新科状元一身明红袍子,帽檐上攒着碧色宫花,跨着轩昂的白马自御街前游过,正是要去赴宫里琼林宴。
待到近了,却见马上之人面庞分明是刀削斧凿的硬气轮廓,偏生五官细致已极,眉目间一点倨傲,一点孤淡,总跳不脱几分青稚之气,脊背却是挺得笔直。
“听闻这新科状元程凤常只得一十五的年纪,风采倒是过人”,桌对面的人斜斜斟了杯酒,又递了个意味不明的眼神过来:“苏大人……比你往昔如何?”
苏鹤姿不答,一仰脖子喝干了杯中的温酒,心中暗忖:“如此美人,他朝必是要会上一会的!”
而再投出窗外的目光,便多了点咬牙切齿的意味。
流水似的年华,多少精彩人物走马灯般离了去了,而程凤常这个人,却为着从未得到,亦从未失去的缘故,便如那句带着三分戏谑的誓语一样,端端地留在了苏鹤姿的心头,留成了他久别的故友。
风尘仆仆,是不宜与旧友重逢的。
苏鹤姿是最爱漂亮的一个人,贪风贪月,贪良辰美景,更贪绝色。幸得他自己的那几分颜色,也美得有点绝。
程凤常走近了看,忽见苏鹤姿一头发丝还散着湿意,浅浅的水渍洇在白袍上,无端地便觉得庭中这片秋意的月光……有些寒。
虽是无意动了心弦,他却未曾打算同苏鹤姿深交,眼见天色已浓,便开口道:“苏大人车居劳顿,还是早些回去歇息吧。”
苏鹤姿“哦”地应一声,也不肯移步,歇得半刻才道:“如此,苏某便回去,他日常来常往,还请程大人莫要辞了苏某。”
语毕,却也不等程凤常答话,转身便走了。
是时风起,满架的伞亭亭秀秀高高低低地荡转开来,荡得院中又静又凉。
照眼望去,苏鹤姿那一身雪白的衣服并那张妖冶的脸反而模糊了,程凤常记住的,是一派脉脉天光里,云边那几点疏淡的星子,和提在他手中,那盏摇曳的,将灭未灭的风灯。
苏鹤姿未见得是个言出必行的人,然而说予程凤常的话,却从未作过虚言,连着这句“常来常往”竟也真得实打实。
苏鹤姿是太子近臣,程凤常为着这个“程”姓,自然是归了安平王爷的。明面上,私底下,该捞的银钱,该使的手段,谁也未曾放过了谁。然而苏鹤姿隔三差五地来,程凤常也鬼使神差地不推辞,他来了,便办一桌席,两人对坐互饮。只是这一样的酒,入到各人肺腑里,却是不同的味。
程凤常再喝,似乎也喝不出几分熟稔来,仍是那副不咸不淡礼数周全的脸嘴。苏鹤姿看在眼里,却也不十分着急,两人各自心照不宣地,堂而皇之地维持这不亲不梳的往来,旁人看在眼里,竟瞧出几分莫逆于心,奈何势不由人的情味来。
势不由人是不错,莫不莫逆,也只得二人心知肚明。
冬来雪大,扯棉撕絮地落了半日,到未中时分才渐渐收住些,换做米粒大小的细雪珠子。程凤常坐在花厅里百无聊赖地翻着一卷书,向窗一抬头,便瞧见家仆引着苏鹤姿从园子里进来了。
却并非程凤常目力过人,实则是那般翩跹临风踏雪惊鸿的风姿,除了苏鹤姿,断不会是他人。
程凤常心头一动,赶忙移开目光去看烧得通红的炭火,待苏鹤姿进了厅堂,再迎上去的目光里无端地多了些末的热意。
苏鹤姿一笑,随手解了大氅,怀里抱着一小坛子酒。
“天寒雪紧,苏兄这是……”程凤常斟酌着字句,却也未知自己几时将“大人”二字去了,唤作一声“苏兄”。
“今日得了一坛陈年花雕,便寻思拿来换两盏香茶饮”,苏鹤姿自在得很,等浓香的花雕已温在霁青色的玲珑小壶里,才慢慢吐出另半句话:“对雪独酌,怎及得上围炉煮雪。”
程凤常不由自主地挑了挑眉,心道苏鹤姿这么个要来便来要往便往的人,原来怕孤清冷寂。而独对庭中那片明晃晃的雪光,确也凄凉。
酒是一杯一杯喝着,渐渐便喝至微醺。苏鹤姿一双眼迷离不定,偏生又亮得仿佛要淌出水。程凤常倒像是入了定般不摇不动地坐着,连言语都愈发少了。
苏鹤姿盯着他的脸瞧了半晌,“嗤”一声笑出来,“‘围炉煮雪问禅意’,程大人可是问得了什么真禅?”
程凤常不深不浅地看他一眼,未曾答话。
“依苏某看来,程大人未必真是六根清净五蕴皆空”,苏鹤姿戏谑地勾着半边嘴角,举手又饮尽了杯中的酒,“若非欲念翻腾,怕也难使得这般机关算尽的好手段……”
程凤常不接话,暗自挑了挑眉角,苏鹤姿不胜寥寥地笑了笑,“苏某同程大人一般无二,不过醉心于风月多些罢了。”
原来彼此均是心知肚明,他朝也就谈不上谁辜负谁。
及至入夜,雪又大了起来。
“曲园里有出折子戏,程大人许是没听过”,苏鹤姿歇了盏,眼酣耳热地半歪着身子倚在榻背上,有意无意地望朝窗外白晃晃的雪光,缓缓道:“那戏文,讲的是山中狐仙恋上世家公子,于大雪天幻作远客寻至府上,二人相言甚欢,颇有惺惺相惜之意。临近夜深,狐仙料定公子忍不下心撵他走,笑向公子道‘雪天留客天,欲留我不留?’殊不知……那公子的心肝竟比霜雪还冷,只应他一句‘雪天留客,天欲留,我不留’。”
程凤常恍若未闻,却有冻风穿堂,吹得灯火一歪,“啪”地爆了个烛花。
苏鹤姿垂下眉目,半晌才续道:“……如此,苏某便告辞了。”
程凤常也不挽留,站起身来随他慢慢走出去。
“……倒还真是痴心意错付冷心肠的旧事”,苏鹤姿絮语般低叹一声:“这折戏,便唤作‘踏雪探情’。”
“仙凡有别,总归是殊途”,程凤常终于接了话,仍旧是那无波无澜的语气,“还是各自上路好。”
苏鹤姿像是早便料及一般对这冷冰冰的言语毫不挂怀,只是斜飞着眼角莞尔道:“天寒雪紧,归途遥遥,程君可否赠苏某一把伞遮遮风雪?”
程凤常忽地停了脚,蓦然立在积雪盈尺的庭院中,往苏鹤姿的背影深沉沉瞧一眼。而那人仍旧不紧不慢地踏雪而行,翩翩然,几欲乘风。
“苏兄……”,程凤常狠地吸了口气,阖目答道:“必备有车驾相待,又何需程某的伞。”
许是听出了他语气中掺在刮骨冷风里那点咬牙切齿的滋味,苏鹤姿反而餍足地叹了叹,方才撩开帘子钻入候在一边的马车里。
窗外落雪愈大,扑在帘子上簌簌有声。
“踏雪探情逢冷心啊……”,苏鹤姿伸手笼住火炉子浅浅凝眉,脸上一个笑,笑得意味深长,“却也无妨。有心,便有情。”
恩怨由天,爱恨由人,反正来日方长。
长长短短的时日中,他追求他的抱负,他沉迷他的风月。那场踏雪探情,无声息地化作了水,似程凤常未干的纸伞,似苏鹤姿发端的湿痕,隐秘地渍在某处,洇开一滩晦暗的印子,霉斑般悄无声息地滋长开来。
朝中使人来拿他下狱那天,苏鹤姿十分平静。自古成王败寇,他倒有点感激这斩乱麻的刀来的快,反正他活着,风华倾天卓绝一世,死到临头也就没有什么不舍。
坊间自然是有些流言蜚语的,极不堪者,甚至编排戏文来明嘲暗讽,苦心痴意偏遇薄情寡恩,春风一度遭逢釜底抽薪。
程凤常不曾辩白一句,不曾过问一声,更不曾至狱中探他一次,望他一眼。
他设的局,同他制的伞一般,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完得清清静静明明白白。只是心底里有意无意地贴着个鬼魅般的印子,不触无妨,若是触及,还是有些伤怀的。苏鹤姿这样浓洌的一个人,倘若断送得籍籍无名,杳渺无声,便是连程凤常也有点于心不忍,能成全他如此隐秘而旖旎地流芳百世,程凤常也不介意担些刻薄的声名。
程凤常没什么于心不忍,苏鹤姿也没什么心有不甘,料得来日方长,总归还是短了几分。
苏鹤姿没曾想会有脱得牢笼的一天,自然也就没曾想会在牢门口碰上程凤常。打量光景,思来忖去,程凤常如何也不像特意来迎他出狱。
“信和王爷大婚,特意请旨赦了你我死罪,改判流徙”,这一次,程凤常先开了口。
“你我争来斗去,想不到如今竟是承了个不相干的恩情”,苏鹤姿挑着嘴角一笑,眼风斜睨无常世事,再道:“到底是殊途同归……”
程凤常笑了笑,未曾答话,只是沿江而行。
苏鹤姿举步相伴,入程府旧堂,穿庭院故道,至西院小室。
正值日落黄昏时分,翠竹芳草,满眼凄惶,又飘起绵绵细雨。
程凤常立在墙边,窗外是一江碧水无情,滔滔自东流去,漏雨苍苔,半点春意如新,梁上的旧燕还巢,卷落一地香尘。
苏鹤姿垂目微笑,浅声道:“我对你……你始终不信么?”
程凤常举目,虚虚实实地朝他一看。
不知为何,苏鹤姿那张素来有些妖冶的脸孔端得是眉目坦然。但像那些眼角眉梢的情绪,到了他的脸上都较他人浓烈三分,动魄时特别动魄,坦然时特别坦然。
他仍旧未曾答话。
事到如今,程凤常愿意信上一信,在他枯寂如尘的人生里,除却算尽机关转圜权术外,还余下一个人似真似假地爱过他。
否则,怎么甘心?
暮雨潇潇,程凤常取过架上那把苍黄色的旧伞,撑在苏鹤姿头顶,两人无言把臂同行。
千秋怀抱半杯酒,万丈风月一盏灯。
不如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