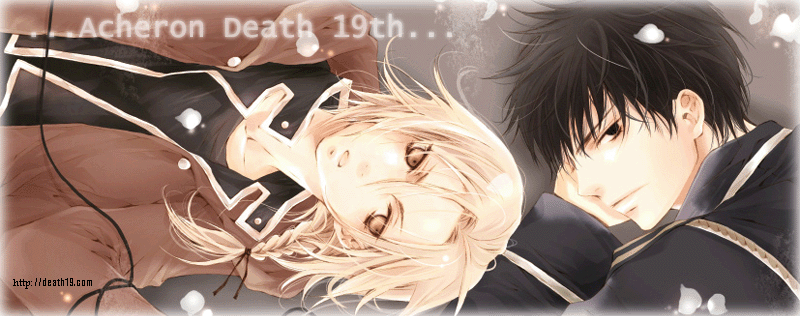番外一 名利场中
裴述母亲即将六十六岁生日,她想回联盟的首都办一场舞会,邀请一些尚且在世的老朋友,重温年轻时在豪华酒店消磨时光的夜晚.
定好酒店后,裴述替母亲发了不少邀请函,发给她的故友,发给几位自己的亲密朋友,其中也包括陈泊桥。
陈泊桥顺利退役后,裴述继续留在北方为陈泊桥处理暗中的事务,他们延续了父辈的关系,既是至交好友,也是合作伙伴。
自总统弹劾案彻底结束,两人台面上的联系比从前稍密切了一些,两个月之前,裴述参加了陈泊桥和章决的婚礼。
当收到请柬,得知婚礼将在亚联盟南部一家新开业的七星酒店举办时,裴述并未惊讶,因为这家酒店是兆华能源的物业,占地很大,十分幽静,陈泊桥选在那里,不足为奇。
裴述以为按照陈泊桥不喜张扬的性格,会在酒店办一场简单的小型私人宴请,但几天后,裴述到桥牌俱乐部喝酒,从一个富商那里听说了酒店休业的消息。
那位富商本要带太太和孩子去南部度假,打算住在那家酒店,但未能预定成功,因为酒店为了筹备两周后的婚礼,已经暂停对外招待。
从俱乐部出来后,裴述想给陈泊桥打个电话问问: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停业是不是太早了。
但他坐进车里,拿出手机看了几秒,却了收起来。
婚礼当天,在众人复杂的眼神中,特邀记者镜头的见证下,陈泊桥给了章决一场盛大奢侈的仪式。
两国高官名流的神情全都有些微妙,仿佛是到了此刻,人们才纷纷确切地记起,除了曽蒙冤入狱的亚联盟前军官之外,陈泊桥也是兆华能源的继承人,亚联盟首富陈兆言的儿子。
仪式后,餐会开始,伴随着乐队演奏的音乐,陈泊桥和章决一起,接受宾客的祝福。章决穿着合身的深色西装,头发规整地梳在颈后,看起来有些紧张和苍白,但很漂亮。
不知为什么,陈泊桥的表情比往日都要严肃,但不论眼睛看向谁,都始终扣紧章决的手,不曾松开过。
裴述的身份是陈泊桥的旧同学,不便表现得太亲近,站得不近不远地看着。
他想起泰独立国那间几十平米的又小又旧的安全屋,和那天陈泊桥看见淋了雨的章决,提问时刻意压低的声线。
裴述想,其实一切都有预兆,只是当时的自己不愿相信——陈泊桥可以想出一万条理由拒绝别人,但当他接受别人的花时,原因只有一个。
突然间,裴述放在内袋的手机震了震,他拿出来低头看,最近打得火热的一个Omega看热闹不嫌事大地给他推送了一条新闻链接:爆炸新闻,陈泊桥今晚大婚的独家政治内幕。
又问他婚礼现场如何。
在这种时刻,裴述着实不该关注此类新闻,但他还是点开了。
独家内幕的撰稿人称,陈泊桥延续了父亲母亲的悲剧,这一次的联姻形式大于内容,还言之凿凿地说,陈泊桥和章大臣的儿子不日就会宣布分居。
裴述看罢,有些啼笑皆非,没回Omega短讯。
大概即使到了北蒙成为亚联盟第十五个附属国,赵总统无罪释放的时候,陈泊桥也不会和章决分居。
母亲生日前夕,裴述和那名Omega和平分手了。他抽了一天,在家陪母亲和已经抵达首都的助理沟通寿宴布置的细节。
确定所有事项后,母亲忽而问起:“泊桥来不来?”
裴述摇头:“还不清楚。”
赵琨的总统职务被罢免,亚联盟即将在三个月内重启大选,兆华能源资助的候选人已赢得党内选举。
裴述看过陈泊桥的行程单,清楚陈泊桥有多忙,因此在陈泊桥给他回复前,他都不确定陈泊桥有没有空出席。
到裴述和母亲前往首都那天,陈泊桥打来了电话。他说一定会出席伯母的寿宴,又问裴述,请柬上说的携伴出席是不是认真的。
“当然,”裴述扶着母亲走上舷梯,问,“章决愿意来?”
陈泊桥说愿意,又说打算多带章决出来见见人。
“怎么?”裴述听出陈泊桥话里有话,便试探着问,“他在家待不住了?”
“不是。前阵子怕他累,没怎么带出来,”陈泊桥平淡地说,“有人坐不住了。”
陈泊桥说得含蓄,裴述却随即想到他前几天看到的消息。
消息称陈泊桥在北美被人下套,标记了章决,两人是奉子成婚。
想来应该是陈泊桥施压,第一家刊登章决孕检单的媒体隔天就公开道了歉,然而道歉也已无法阻止流言的扩散。
媒体对章决的质疑或许永远不会消失,但裴述还是诚恳地说:“带来吧,我这里肯定没人敢闹事。”
2.
参加裴述母亲生日宴的前一天晚上,陈泊桥原本要在亚联盟西部的子公司厂区过夜,不过这一次的事处理得比想象中快,不到五点,所有日程结束了。
秘书向陈泊桥报告后,陈泊桥当即决定提前返程。
从西部城市到首都家中,花费了七个多小时,陈泊桥进房间时,时钟已经指向零点,但章决还没睡。
章决穿着常穿的浅色丝绸睡袍,背对着卧室正门,坐在书桌前托腮翻书。陈泊桥开门的声音惊动了他,他回头来看,见到陈泊桥,微微愣了愣,过了几秒,又下意识看了一眼钟。
陈泊桥背手将门关上了,没有往前走,调侃章决:“原来我不在的时候,有人睡得这么晚。”
章决抿了抿唇,像是隐约地笑了一下,放下了书,站起身,向陈泊桥走过来。
他走得有些慢,但是步履还算轻盈,他怀孕后没涨太多体重,宽松的睡袍遮住了腹部,几乎看不出线条,但或许是信息素影响,他面上终于有了些血色,嘴唇也变得红润少许,气质温和了一些。
走到陈泊桥身前,章决展开手臂抱住陈泊桥的腰,仰起脸,然后闭上眼睛,陈泊桥便低头吻他。
杏味混着沐浴液的香气,被三十七度的体温蒸出一股暖意,章决的嘴唇温软,舌尖湿润,很滑也很甜,微微鼓起的肚子轻顶着陈泊桥的下腹,他舔舐陈泊桥的上颚,吻得很纯情,像在强调,自己没太多别的意思。
吻了少时,陈泊桥稍稍移开一些,对章决解释:“事情提早办完了。”
章决睁开眼,看了陈泊桥一小会儿,侧过脸,“嗯”了一声,又将脸颊贴在陈泊桥的颈窝处,睫毛刷在陈泊桥的皮肤上,抬起头,吻陈泊桥的下巴。
陈泊桥细数过,自己逗章决、不给章决吻的次数,好像也并不是太多,却真的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打消章决在想要索吻时的没必要的迟疑。
“……想你。”章决说得含含糊糊,
陈泊桥搂着章决的腰,站了几秒,又让他贴紧了自己一些,含住他的唇。
吻渐渐变了味道,陈泊桥把章决抱起来,往床边走。
章决的睡袍带子永远系不牢,陈泊桥没碰就开了。
或许是因为太瘦,章决怀孕五个月,小腹却只是略微隆起,从肋骨下方几厘米的地方开始,白皙的皮肤向上拱出一道很小的、圆圆的弧线,圆弧顶端甚至还没超过肋骨最高的地方。
不过上周检查时,医生倒说孩子发育得很好,生**情况也很稳定,让章决不必担忧。
陈泊桥低头,没什么表情地看着章决的小腹,让章决觉得有些难为情,拉着睡袍想把肚子遮好,但指尖还没碰到衣摆,手腕就被捉住了。
从章决怀孕起,陈泊桥就没碰过他,这是他们几个月来第一次这么亲近。陈泊桥不轻不重地把他往下压,沿着腿根滑到内裤的凹缝处,指腹轻轻往里顶,让布料磨着章决流水的地方。
“都这么湿了。”陈泊桥垂着眼,拨开布料,用两指撑开入口,缓慢地模拟进岀。
房里很近,只听得见很轻的水声和章决微颤的呼吸声
“怎么办。”陈泊桥低声问他。
章决湿得厉害,水不住往外滴,只是手指碰着,他就高潮了一次,张开了腿,腿根微颤着,抬眼看着西装革履,一丝不乱的陈泊桥,伸手去解陈泊桥的皮带扣。
陈泊桥也很硬,鼓鼓囊囊地顶着章决的手背,但章决要再往下解开他的裤子时,他把章决的手按住了。
“章决。”陈泊桥叫章决名字,意思章决也明白,是今晚不做。因为医生说的稳定,只是对章决而言的稳定,不是能随意做爱的稳定。
章决愣了几秒,慢吞吞收回了手,他仰起脸,问陈泊桥:“那我给你……”
“不用了,”陈泊桥低头啄吻章决的脸颊和嘴唇,扯了纸巾把章决腿间的湿痕擦干了,说,“我洗个澡。”
陈泊桥大概确实只是冲了澡,等生理反应下去就出来了,他穿着比章决大一个号的睡袍,走到床边。
章决左侧卧闭着眼,给陈泊桥留了一盏床头灯,陈泊桥上床前关了灯。章决安静地等着,等陈泊桥的体温从背后贴近。
陈泊桥结结实实地从后面抱住了章决,胸膛贴着章决瘦削的脊背,吻了曽吻过很多次的章决后颈的伤疤,手覆在章决的腹部。
“章决——”他贴在章决耳边说。
他们抱着睡了几个月,章决听见陈泊桥的声音响在耳边,心跳还是下意识地开始加速跳跃。他没动也没说话,想要听陈泊桥继续对自己说话,但陈泊桥静了下来。
过了许久,陈泊桥才说:“什么时候才能标记你。”
他的声线很平,比他接受采访或者和下属说话时更平,好像懒得再装出温和潇洒的样子,低声附在章决耳边,用十分冷静的语调说不够冷静的话:“不想等了。”
3.
傍晚七点开始,裴述母亲的宾客陆陆续续来了。
陈泊桥征询裴述同意后,事先让人放出过风声,说自己将携伴出席,此刻便有不少记者杵在酒店附近,扛着长枪短炮,想拍得陈太太的一手照片。
快到酒店时,陈泊桥给裴述打了个电话,裴述带着新伴出去接他。
加长的行政轿车停下后,门童上前打开门,陈泊桥先下车了。
不远处的照相机闪光灯亮起来,陈泊桥像没看见一般向裴述点头示意,又转回身,俯身,向车里的人伸出手。
一只苍白细瘦的手搭在陈泊桥手心,陈泊桥合手握住了。
章决被陈泊桥牵下车,他穿着半高领的黑色薄毛衣,头发剪短了一些,腹部微突,抬眼看了看裴述,微微颔首,裴述也努力地对章决露出了一个自认为友善的微笑。
陈泊桥轻轻地揽着章决的腰,走近裴述。
裴述引他们去舞厅的一个圆座坐下,他要替母亲招呼客人,没久待,不过一直留意着那头的动向。
似乎时常有人去向陈泊桥问好,章决静静地坐在陈泊桥身旁,他们坐了一会儿,乐队换了一首慢华尔兹,陈泊桥向章决伸手,章决搭着他站起来。
全场的目光都看向他们,但陈泊桥和章决都并未在意,不疾不徐地在舞池边缘跳了一支舞。
待舞曲奏毕,他们又走回座位,陈泊桥的助理突然进来,俯身和陈泊桥交谈几句,陈泊桥凑到章决耳边,不知说了什么,章决点了点头,他才接过助理手里的移动电话,向裴述走来。
“我出去接个电话,”陈泊桥对裴述道,“替我看着点。”
裴述的新伴挽着他的胳膊,好奇地看着陈泊桥,裴述答应下来,陈泊桥和助理走出舞厅,刚要带着伴去章决那边,母亲和一个太太站在一块儿,喜滋滋地叫他名字,叫他过去。
他只好让新伴先站着帮他盯着,先去母亲那儿。
原来那位太太是母亲的发小,恰好认识一位适龄又与裴述家世登对的Omega,母亲便十分想撮合裴述和对方见一面。
裴述听着都觉得头大,随便聊了几句,找了个理由先溜了,但回过头,却找不到章决,也找不到自己的新伴儿了。
他刚想给新伴打个电话,忽而在远处通往室外的落地窗帘边看到了他的背影,便快步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语气不佳道:“不是让你看着么?”
新伴神色有些慌张,细声细气道:“就在外面,有个人和他一起边说边出去的,我又不敢拦,只能跟过来了。”
裴述皱了皱眉,走出了门。
春夏之交的燥热气混着树叶和草香迎面而来,舞厅外的灯光不算太亮,周边有些小雕塑和高树,还有几条亮着落地灯的鹅卵石小道。
他一开始没看见章决,正欲再走出去找找,却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
“毕业后就没再见过你,”那人说,“不过我见过陈先生一次,他送我弟弟回家。”
裴述又往前一步,恰好看见树林间的小观景台上,与章决对话那人的侧脸。
他愣了一下,继而想起,那人是母亲旧友的儿子,也是他们在罗什的一个beta同学,似乎还有个Omega弟弟,曾和陈泊桥约过一次会。
裴述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有一阵子,陈泊桥和他弟弟约会的照片在媒体上登得铺天盖地,连一向不关心这些的母亲都问了他好几次,问陈泊桥和她朋友的儿子是否真的在恋爱。
感情是来示威的。
裴述一阵头大,不清楚章决为什么会跟他出来,刚想上前去打圆场把章决带走,却听见章决说:“是么。”章决声音很轻,听不出情绪。
“是啊,我还知道你和艾嘉熙的事。”那人压低嗓子,对章决说。
“哦?”章决很随意地应了一声。
他的语气让裴述隐隐觉得熟悉。裴述看着树影中那两位,思索着什么时候听见过章决这么说话,章决就稍动了动,靠近了那人少许。他比对方高小半个头,背对着裴述,微微垂着脸,温吞吞地反问:“我和艾嘉熙有什么事?”
裴述倏然间想了起来,在上学时,章决大多数时间都是这么说话的。也许是因为现在他和章决见面时,陈泊桥都在场,他就忘了原本的章决是什么样的了。
那人好似乱了阵脚,急促地笑了笑,说:“你别装傻。”
“我不知道啊,”章决又靠近了那人一点,不冷不热地说,“不如你告诉我。”
那人往后退了一小步,裴述犹豫了一秒,还是开口了:“章决。”
章决的背直了直,不过没回头。那人看向裴述,裴述没理他,对章决说:“我在找你呢。”
那人嘟哝着对裴述解释了几句,说自己在和章决叙旧,见裴述和章决都没回应他,便匆匆走了。
裴述走近了章决几步,章决将手肘支在观景台的大理石罗马柱旁,看山下的景色。
“找我?”章决没转头看裴述,只是平淡地询问,“他回来了吗?”
“还没有。”裴述说。
章决便不作声了。
舞厅里与外头比,确实太过嘈杂,裴述也想避一避,便没立刻走回去,随口和章决聊天:“没想到泊桥不在,你还挺凶的啊。”
章决看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不说话。
裴述笑了笑,转眼恰好见到罗马柱边可以弹烟灰的小凹槽,想起章决在泳池边焉巴巴抽烟的样子,忍不住问:“你真戒烟了?”
“嗯,”章决说,“戒了。”
裴述觉得章决一抽就是半盒,能为爱戒烟也够感人的,半真半假道:“你知道吗,有个去烟味牌子做的漱口水和香水,抽完烟一用,警犬都闻不出来。”
章决闷了半天,站直身,无奈地说:“你别害我。”
“我怎么敢啊。”他又说。
裴述手机又震了起来,陈泊桥给他打电话了。他接起来,陈泊桥就问他:“章决呢?”
“在外面透气。”裴述说着,给章决作了个请的手势,两人一起往里走。
4.
回场后,裴述漂亮的新欢挨了过来,笑吟吟地拉住了他的手。omega的手掌很绵软,如同上好的绸缎,指尖挠着裴述的掌心。
“没什么事吧?”他问裴述。
“没事。”裴述说。
余光里,裴述看见陈泊桥从后面搂着章决,贴在章决耳边说话。
章决听了一会儿,叫住了端着花盘的侍应,从盘中择了一支玫瑰,送给陈泊桥。
陈泊桥抽走玫瑰,自然地吻了他,吻得短促,也吻得放肆。
富丽堂皇的酒店大厅中歌舞升平。
人人都打扮得光鲜亮丽,裙摆飞扬,觥筹交错,但眼神都偷偷停在接吻的人身上。
裴述可以想象今天过后,又会有多少流言蜚语开始流传,但他不再觉得章决与陈泊桥不登对,只是想自己是不是也该找个人定下来。
因此他邀请omega跳了这天的第一支舞,跳给轻浮,跳给肤浅,跳如鱼得水,跳俗不可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