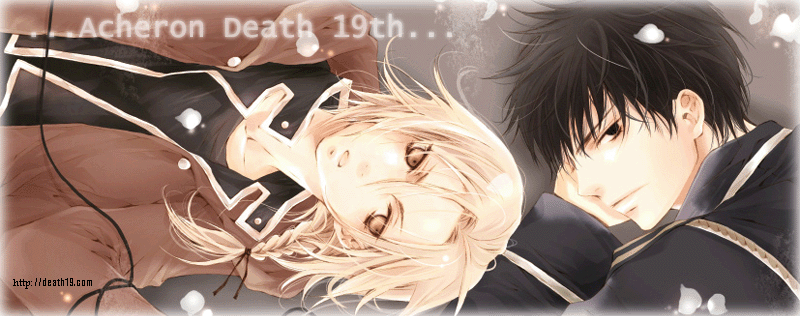番外Memorize
差点错过站头。
运行状况几乎处于半废弃状态的“沃尔沃”客车如同暮年的老驴,运载了超过他承载力的乘客以及他们随身携带的行李,跌跌撞撞通往小城临海的郊区。车顶空调制造着嗡嗡的噪音,乏力的吐出缺乏凉意的气流。车内间或生出说话声,汗水、生鲜、体臭混合成古怪的慵懒味,旅途疲惫的浓郁睡意弥漫了车厢,被人们吸入肺里。
他,外来者,自很远的另一个沿海城市而来,运气不佳的买入最后排右侧靠窗位置的车票,座位下面是排气管,每次轻微的刹车,就能感到负载过重的老客车重重吐气的震动。车子开动后,后置的空调烘烤着座位,车座下的排气管致使脚边涌起热浪,衍生燥热的困倦。
出站不多久,他进入了令人不快的属于过去的真实梦境,几小时后,如果不是售票大妈的报站——尖锐但在发音途中剧烈颤动的嗓音与美国惊悚片里的尖叫如出一辙,把他自过去的梦里生硬的拉扯出来,他差点错过站头。
迷迷糊糊的听到站名,恍然是自己的下客站,打着呵欠拎起背包,跨过过道上推积的各种颜色的蛇皮袋和箱子挤到门口,向售票大妈询问目的地的方向,接着在车停下后跳下车去。
那站仅有他一个人下车,身后,估计是离合器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喊叫,软绵绵的悬吊犹如车轮碾压在一大块海绵上,没有紧张感的震荡产生慢三步舞的节律,它就那样摇晃着屁股气喘吁吁的开走了。
不多久,四周寂静下来,远处的海边传来海浪声。
车站,其实是一块被金属棒顶着的铁牌,白底和红字的油漆大部分已经磨损,只能依稀辨别字迹,确实是档案里提及的地名没错。
野草,石头,零星的砖瓦房,带咸味的风,烈日,平直美丽但少有车辆驶过的柏油路……这里具备了流放地的特质,如果班车不再返回这里,他不会觉得意外。
手背抹掉下巴上滴落的汗水,从背包里取出记录本,翻开,重新确认了地址,眯着眼朝太阳的方向望了望,低下头拉下鸭舌帽的帽沿,往西走去。
走过两个岔口,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在砖瓦房也看不到几间的小地方出现了漂亮的三栋欧式建筑,被黑色铁栅栏围拢,如同沙漠里的绿洲,档案记录里提到,它是一所具有实力且设施完备的特种疾病疗养院,为无法在人类沙漠生活的疲惫旅者提供最后的栖息之所。
清晰的空气,离海不远的位置,远离喧闹的生活,足够等待死亡的病人在夜深人静之时获得片刻安宁,他可以想象,那时,只需屏息凝神,海浪敲打岸边礁石的拍击声将轻柔的传入耳中,声声不息。
他只认为这里是一座漂亮的监狱,关押着即将行刑的死刑犯。
疗养院没有保安,几乎可以长驱直入。这里在普通人眼中无异洪水猛兽,它没必要为自己防备。
铁门虚掩着,他伸手推了一下,在轻微的摩擦声后向他展开。
夏日正午,太阳下烫热的水泥地上无人走动,但房间窗口可以看到偶尔晃过的人影,他打量了一下,走入最近的棕色房子。
棕色房子底楼设有接待处,空调打出适和的温度,一个长雀斑的小护士趴在接待桌上翻阅杂志,两个老头坐在不远处的藤椅里,他们中间摆着桌子,桌子上有棋盘,两人并不交谈,只是自顾自的下子,似乎没有注意到闯入者,或者只是兴趣寥寥。
“你好。”
小护士才注意到有访客,不好意思的把杂志合拢,是一本《嘉人》过刊。
“您好,请问需要什么帮助么?”把杂志搁在一边后,小护士用手肘撑着桌子,好奇的看着陌生访客的脸。
“我想来看一位朋友。”
“您有预约么?”她从桌子的抽屉里取出一本黑面抄本。
“预约?”
小护士点点头:“访客都需要提前预约,并且必须先征得病人或者病人家属的同意。您没有吗?”
访客取下背包:“他和另一个我的朋友一起消失了快两年,很不容易打听到他的讯息,我想来确认他是否在这里,因为后者的父亲非常担心他们。”
“抱歉,我们这里是不允许随便透露病患隐私的。”
他了然的笑了笑,让小护士有点脸红:“是不是能见面其实不重要,你知道这种病的破坏力,我只想为朋友的父亲确认他们是否还活着,你能帮助我吗?你只要看看是不是照片里的人就可以了……”
“那个父亲等待儿子两年只得到一张轻飘飘印着向日葵的明信片,以及想念,”他顿了顿,看着她,“你一定能体谅他的心情吧。”
半小时后,他见到了院长蔡慧民。
蔡慧民是个五十多岁的瘦小女人,头发盘起,有一些白头发夹杂其中,眼睛下面带着厚重的眼袋,眼神清澈,看上去很精神。
“您好,”蔡慧民露出让人产生好感的微笑。
“您好,院长,”访客看了看那两个摆棋子的老头,“可以的话,借一步说话。”
“最初是依靠六个月前的明信片邮戳,基本锁定区域,但是附近医院都没有他的讯息,后来才把范围扩展到相关的医疗站,包括疗养院,但是疗养院的数据更新并不及时,上月初,我才从贵院的数据库里调到一年前的治疗记录,其中可能包括我要找的人,名字和年龄等基本信息符合,但因为没有照片所以还不能确定,”访客把一张照片复印件递给蔡慧民,“在外貌上会有些差异,如果他还活着,应该在二十五岁左右。”
蔡慧民接过照片看了很久,并没有否认的意思:“考虑到疾病的特殊性,我们不要求病人提供照片,甚至对于某些信息的真实性也并不苛求。”
“您见过他?”访客看上去有点兴奋,“是一个高大的男人陪他来的么?”
她把照片还给了访客,有些谨慎的望着他:“这里的数据库是绝对保密的,只有总院有记录,为什么您能看到这里的数据库?请问您和他是什么关系?”
访客接过照片,取出证件,展开:“他和某个案件有牵连,希望您能配合我的工作。”
“抱歉,作为医生我不能透露患者的信息,”蔡慧民看了一眼证件,向后退了一步,采取了近乎不合作的态度。
访客收起证件:“我可以理解您爱护患者的心情,不过这不是明智的行为。”
蔡慧民沉默了一会儿:“这个孩子犯罪了么?”
“不,他没有。”访客给与确定的答复。
像是要确认他说的是否属实,蔡慧民长久的打量着他,最后妥协了:“好吧,但这些未必对你有用……我并不想妨碍您办公,疗养院,尤其是收治这一敏感领域患者的疗养院我们有义务对于患者的隐私保密。”
“是,我理解。我想知道,他还在这里么?他还活着么?”
蔡慧民泡了茶递给访客:“我冒昧的问问您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
访客吹开水面上的茶叶:“他是重要的证人。”
“证人?那您无需再去找他了。”
访客抬起头。
“他的状况是无法出庭的……即使他还活着。”
访客张开嘴,连开始烫手的杯子也忘记放下。
“他怎么了?他们不在这里?”
蔡慧民背对着他脱下白大褂,挂上衣架:“他们三个月前走了。”
“离开前,除了带他来的年轻人,他谁也认不出了。”
“……怎么会?”
“罹患这种疾病的病人中,有一些会出现大脑受损的情况,那孩子就是其中的一个,”蔡慧民发出轻轻的叹息,她走到办公室底端的文档柜前,戴上眼镜,用随身携带的钥匙打开橱柜,翻找文件。
一会儿,她拿着一叠文件回来,递给访客。
“这是那孩子的治疗记录,最后一次手术发生在七个月前……二十个月前到这里时,他已经发病了,但病情发展缓慢的令人吃惊,也许是有人支持,也许只是运气……尽管这样,术前,他的一些脏器因为肿瘤开始衰竭。”
访客快速的翻阅,最后停在末页:“这里写了,手术成功了?”
“不能这么说,不过作为延长生命的初衷,手术倒可以称为相当成功。”
访客抬头,注视着在对面沙发坐下的蔡慧民:“那个男人带他去哪里了?”
蔡慧民摇摇头:“我不知道。”
“院长,请不要感情用事!”声音焦躁起来。
“术后三个多月,他们在半夜里走了,第二天,一个小护士发现疗养院的一辆吉普也消失了。”
“他不会偷东西。”他笃定的反驳。
“他们没有,年轻人把他的大奔车留给了这个地方,因为他答应把那辆车作为附近农户儿子结婚的婚车。”
“他也不是会考虑别人感受的人。”说完,访客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公正的立场。
蔡慧民没有争辩什么,发亮的眼睛似乎能看穿访客的焦虑,那眼神让访客更不安了。
文件上确实没有最近三个月的纪录,避开眼神,把文件合上,他站起来:“很抱歉,这份文件暂时不能还给您,请见谅。”
蔡慧民耷拉着眼皮,显出一个遗憾的表情。
在把访客送出办公室后,蔡慧民靠着门框看着他下楼。
“那个感情用事的人,其实是警官您吧。”
访客停下脚步,然后继续往下走。
“两个人,一个块头很大,总是板着脸,不怎么笑,说起话来冷言冷语……总之看上去挺厉害、不太亲切的男人,三十岁不到,他身边有个小个子,很温顺,很忧郁,比他年纪小一点……这份档案就是他的。”按着两年前记忆里的样子,没有使用职业的叙述方式,他相当直感的描述着。
“你在找大狼和小狼吧?”因为拿到了档案,接待处的小护士对他的问题也坦诚了,她抬起头,有点疑惑,“可是大狼不是你形容的那样,他总是帮助别人又很幽默,这里所有的孩子和家长都喜欢他。”
“大郎?”
“嗯,”小护士眼睛弯弯的笑了,仿佛回忆了快乐的情境,连眼睛下的淡棕色雀斑也跟着活泼起来,“他们刚来的时候,大狼做了小城唯一小学的体育课代课老师,被派去参加城里举办的运动会,长跑比赛的时候,小狼画了一只狼的大画像给他加油,大狼赢了比赛之后,所有孩子都管他叫大个子狼,他生气了,就开始叫小狼小狼了……后来大家叫习惯了,几乎没人记得他们的名字了。”
访客听着皱起眉头:“你确定那个小狼是档案里这个人?”
“当然,我还有他们的合照呢!你等一下。”
小护士回去自己的宿舍,然后蹦蹦跳跳带来了一个相框,摸了一下,然后很郑重的递给他:“虽然有点舍不得,这个还是给你吧。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如果你找到他们的话一定一定要告诉我,大家都很担心他们。”
访客出神的望着那相框,慢慢的伸出手,在看到照片之前,他的手指有些发颤。
那是他们离他最近的记忆。
从疗养院离开依然走了很长的路,太阳已经西斜,空气逐渐凉快起来,虽然公车依然闷热难当,毕竟比来时好过了一点。
回程的车人没有来时多,他坐上了中门附近较为凉快的位置,把背包抱在怀里,又像来时那样在摇摇晃晃的车上被摇晃的睡意缠绕住。
在梦里,他脑中虚构的模糊的大狼和中学时代那个阳光少年的剪影一点点融合起来,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人。
这时,他的腹部和抱紧背包的手指感到一阵烫热,他被惊醒了。
背包是热的。
打开背包,那里实在没有什么会产生热量的东西。
他最后盯在那个相框上。
取出相框的同时,塑制相框和玻璃突然变的滚烫,他下意识松开手,捏紧了被烫到的手指。
相框在地上躺着,手指上起了水泡。
他有些莫名的俯视它,所有人包括司机都显出慵懒疲惫的神色,没有谁注意到额上冒出冷汗的他。
海浪的声音。
穿过关起的玻璃窗,穿过客车的马达声,穿过车内弥漫的睡意。
如被什么所召唤,他朝窗外望去:
海,阳光下泛着金色光芒的海!
车子正开在来时因为打盹儿错过的海景公路上,壮丽的海面,闪光的海水里卷起白色浪花,从看不见的海中某处滚滚而来,涌上黄色的沙滩,又退下。
咒语一般大海的心跳。
他捡起相框,背起包,走到车头,拍了拍胖司机的肩膀。
“抱歉,麻烦停一下车。”
大海在离公路很近的地方,路面有缓坡下到海岸。海滩上没有什么人,唯有黄色的沙粒,以及孤独的岩石等待涨潮后大海的怀抱。
他走上潮湿的沙滩,爬上耸起的岩石,望着没有边际,无法捉摸的神秘的海,手里的相框已经变凉了,似乎有什么讯息要从其中探出脑袋,传达给聆听者。
大海开始往岸上走来。
相框变的暖热,并不烫手,他低头凝视着它:
照片上的两个大头,嘴角亮出弧度相仿的完美笑容,发型都是一样土的掉渣,穿着翻领的红色T恤衫,很没品味,小个儿的脖子上挂着六芒星形状的吊饰,大个子的脖子上套着一个草环……他们的容貌本来毫无相似,照片上,却像一对兄弟。
仰视着镜头,因为阳光微微眯着眼睛,大个把手搭在小个子的肩膀上,小个子的鼻子上架着滑到鼻尖的太阳眼镜。
他们正哈哈大笑,这瞬间在快门下化为永恒。
最后看了一眼照片,他把相框扔进海里。
相框在海水里翻动了几下,沉下去了。
我不带走。
他无声地说。
远处公路上走过的当地人朝他善意的挥动手臂,提醒他离开那里。
他会意的点点头,走下岩石,趟入已经没过脚踝的海水里,大步向岸边走去。
——————————————————————
正式完结,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