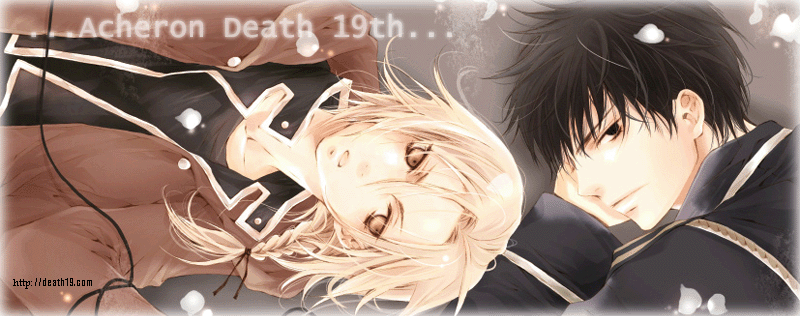☆、番外一:以我所知
陈棋瑜不觉得自己是个多聪明的人,但却也不笨。有些事情,该看出来的还是能看出来。
破绽并不算少,诸如要除掉皇上,毒杀这麽愚笨又明显的谋杀行为,千岁是不屑做的。比如千岁曾在中秋透露时局感叹之意的行为,陈棋瑜又并非看不到。又例如,千岁多是拿贪官和嚣张的贵族开刀,而那些有才有德的忠臣良将,却并不杀尽,只一一发配远方——陈棋瑜不禁觉得这是在帮皇上。他朝朝中一无贪官、二无跋扈贵族,皇上处理事情定然方便得多,再来将才德兼备之士从边疆召回来重用,他们定然对皇上感恩戴德、忠贞不渝,实乃皇上之福。
当然,他也有想不明白的地方,例如九千岁为什麽不澄清——他想来想去,只想到一个可能,那就是九千岁希望自己被诛杀得名正言顺。但这样的理由实在伟大得让人觉得不合逻辑。
另外,九千岁和杨逸凤、鮌教真实的关系又是如何?如果杨逸凤真与九千岁串通,那麽为何杨逸凤要将陈棋瑜弃到白骨坑而九千岁又来白骨坑相救?而且在祥云峡,九千岁的精神状态明显不对,绝不像是图谋大事的踌躇满志,相反更像是进退两难、筋疲力尽。
因为相信——这份相信似乎盲目得不合理,他认为谋朝篡位真有其事,但策划者却另有其人。而陈棋瑜觉得自己的怀疑也很不合理,因为他一开始就怀疑是太後。
这样太不合理了,真的,皇上乃是太後亲儿,太後怎麽会加害於他呢?可是除了太後和九千岁之外,谁能在皇上膳食中下毒?毒杀皇上,嫁祸九千岁,得益的是太後。陈棋瑜在村中昏倒,也是被太後的人带走。不过让陈棋瑜最初产生怀疑的,却是太後给他的毒药。『万境归空』这种毒药,怎会是太後娘娘这种久居深宫之人所有的?这种毒药恐怕只有行走江湖的人才会拥有——而且必须是很有本事的老江湖才能弄到手。如此一来,他不得不怀疑太後与杨逸凤的关系。当年皇上後妃也不算少,九千岁为何独独扶持了这个连妃子也不是女官为太後?如果杨逸凤与太後有什麽关系的话,那麽九千岁帮助太後也说得通了。
而皇上的态度也让陈棋瑜感到疑惑。皇上选择和萍水相逢的封皖同行,却不与太後一同乘搭快船回京。而且皇上秘密回京後严密地躲起来,根本没有让太後知道自己活著的打算,这绝非一个十几岁少年对母亲应有的态度。更何况他与母亲不是在宫中相依为命多年了?感情不该比一般母子更为亲厚吗?带著这种疑惑,陈棋瑜写信试探皇上,问及是否要告诉太後皇上活著的消息,皇上搪塞否决。
但若如此,九千岁的态度是否太奇怪了?太後利用杨逸凤控制鮌教,声讨千岁,暗里又试图谋害皇上,嫁祸千岁,而这些正正发生在千岁眼皮底下。连陈棋瑜这麽个消息不灵通的人也能看出端倪,九千岁又怎会毫无觉察?
如果说九千岁明明觉察了,却又默不作声,甚至到了被栽赃嫁祸、明杀暗杀的地步,也没有明显的反击意图,那又是为何呢?
不过这与聂晨霜透露之事联系起来,便也可信了。因九千岁感念杨逸凤之恩,对杨逸凤之举动百般纵容。但与太後之间,又有何关系?於是陈棋瑜便托青瑾去查探太後出生籍贯之事,再查杨逸凤来历,便觉得大有可疑。陈棋瑜因此怀疑这两人早有瓜葛,甚至是亲人。
九千岁为了报恩,背负奸佞之名,扶了杨逸凤的亲人为太後、皇上。名声於千岁来说大概是身外之物,不比银瓶里的一枝花值钱。因此他也不在意受人误解。
不在意吗?
陈棋瑜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并不是吧。之前陈棋瑜被误解为权阉走狗,其中也有九千岁推波助澜的份儿。也许九千岁也是想用恶名来将陈棋瑜孤立,让陈棋瑜感千岁所感。
千岁多番说『唯有我懂你』,岂非也是想『唯有你懂我』?
也因为如此,千岁在服毒倒下後,说的最後一句话是『你也……该……懂……』。
其实陈棋瑜也不知自己究竟懂不懂。但他知道事情已走到无法调和的一种地步。杨逸凤、太後、皇上、九千岁之间虚假的平和已经接近崩溃,当这面危墙轰然倒塌之时,他也到了抉择的时候。
他很清楚的告诉自己——这麽告诉自己——他当做的是对大多数人最有好处的事,而不是因私情而成全罪孽。『私情』……他想了想,有吗?
既无私情,他又有什麽好犹豫的。
可真的无私情吗?他掸了掸肩上的积雪。
他知道自己不愿意见到九千岁死。一点也不愿意,也不愿见九千岁杀人。他这辈子也没对任何人有过杀意——他本是没有的,只是当父亲死讯传来之时,他便变得不一样了。
父亲明明是个无辜之人,却丧掉性命。他方才知道『冤冤相报何时了』是一句多麽假的话,当活生生还会微笑的亲人被夺去了生命,他怎麽可能不冤不恨。
当时,他一个人坐在冷冷的雪景中,自己也仿佛要成了一个雪人了。他觉得,如果那个时候九千岁在他身旁,恐怕又是不一样的光景了。而那时他想得最多的,除了父亲,就是九千岁。
他想,不幸中的万幸,杀父仇人并非柏榆。
他又想,可惜柏榆不在。他想找人说说话。
他想哭,又想杀人。他脆弱又危险。等到台上的积雪散去後,他的手指都冻僵了,可他的脑袋却回暖了。忽又不想哭了,更不想杀人了。甚至他开始庆幸柏榆不在身旁了。
他知道,刚刚是他最脆弱的时候,如果柏榆在身旁的话,他定会向柏榆求助,会将自己心里的一切向柏榆和盘托出。
这并非『坦白』,而是『投降』。如果他对柏榆露出那样的坦诚的忧郁,那他就是投降了,屈从了,他就要被柏榆支配了。以柏榆那种魔鬼的性格,定然会巧言令色地劝诱他,而那时的陈棋瑜恐怕禁不住这种引诱,很可能真的将会接过柏榆给的刀子,拿去刺杀仇人。那麽,陈棋瑜就算是被柏榆支配了,如果这种事情一旦发生,陈棋瑜就将永远陷落柏榆的黑色中。
陈棋瑜知道父亲不能白死,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杨逸凤和太後杀人了,应当受罚,可此事还是交由皇法吧。饱受了丧父之痛後,冷静下来的他更不愿杀死他人的亲人。可他却不能亲手去杀人,那是一种他固守的软弱和伪善。而太後和杨逸凤都是他的杀父仇人,而太後和杨逸凤仅剩的亲人就只有皇上。而皇上恰好也是皇法的代表。只能让他办了。
皇上对於人命没有陈棋瑜的固执,反倒是眦睚必报之人。他让青瑾引二人会面,是想让皇上直接面对太後。他相信,在宫外,失去了御林军和权力的庇护,太後是无法胜过皇上的。
而太後倒台,覆巢之下无完卵,杨逸凤和鮌教恐怕也无法安稳了。
陈棋瑜就此双手不沾血的解决了这宗仇恨。
末了,他端来清水,帮昏迷中的柏榆洗抹身体,拿柏榆惯用的梳子去梳好头,又挑了一套乾净柔软的衣服帮他穿上,怕他冷著,又为他加了一件红色的大氅,温暖地将他包好。最後,将他送上了马车。
陈棋瑜目送著马车远去。马车带著那个人走了很久,他还呆呆地站著。
马车将去何方呢?
只要是远离京师,那便好了。
希望他醒来的时候别太生气。
================
看完这个番外,我想大家对正文後段剧情会更了解吧!
谢谢在我不更文这段时间还上来投票点击送礼的大家~~~~
看到卫子愉的长评,超感谢!看到长评就很鸡血,想继续写继续写……所以快用长评来砸死我吧!=w=
☆、番外·有缘千里(1)
“熙华十五年,劳营爵陈棋瑜追缉钦犯,至泰山十八盘,三千逆贼围之,五马分尸而卒,命绝升仙坊,时年二十八。天子哀恸,命大将军封皖领兵五千,围剿贼人,血洗泰山,悬逆贼首级於翔凤岭。”
泰山乃是五岳之巅,顶上风起云涌。现下已是黄昏日暮,然而金光漫天,在山上看来,确实气象万千、令人望而生畏。翔凤岭现在都可称为『翔凤陵』了。站在中间一看,左是高耸入云的翔凤岭,右是悬崖峭壁的飞龙岩,中有天然大石相接,是为一线天。夕阳西下,如血的光芒洒满一线天上,只觉险象环生、悲怆萧条。
官道上,陈棋瑜头戴深蓝幅巾,身穿藏青长衫,肩上围著那件已经旧了的软裘,脸上神色悲凉:「不想我一次假死,竟引致如此惨剧。」
侍从青琛说道:「公子,你就算活到一百岁,皇上也终是不会放过那帮武林人的。」
陈棋瑜叹道:「到底这个由头是我。」
青琛说道:「陈棋瑜早已死在泰山上了,这不是早说好的事了么?公子当初是怎麽说的?」
陈棋瑜这才略略回过神来,叹了一口,眼神回覆清明,朗声道:「陈棋瑜早已五马分尸而死,命绝泰山。而我乃是俞无念,不与江湖恩仇有碍,也不与庙堂朝廷有忧,只是一青山绿水间的自在人。」
青琛笑道:「这可不错。」
陈棋瑜——此刻该是俞无念了——俞无念又说:「你还跟著我?」
「我怕公子一个人行走江湖会吃亏。」青琛笑道。
俞无念笑了笑,道:「也是,我这人手不能挑、肩不能抬,一个人固然是活不下去的。多得你不嫌弃。」
青琛笑道:「公子於我恩重如山,我要是不报的话,倒是会折福折寿的。」
俞无念与青琛说说笑笑,很快就进了城。城里没因泰山的惨剧而发生太多的变化,百姓们依旧是吃饭打屁过日子,虽然是心狠手辣,但皇上对待百姓确实很宽厚。
陈棋瑜当初还怕皇上性情暴戾、非万民之福,此刻看来,恐是多虑了。陈棋瑜辅助幼主,现下皇上已成人了,羽翼已丰,君临天下,他大可安心退隐,不再沾染朝野纷争。
青琛跟著俞无念走著,却见前头有个些人在客栈前围著,议论纷纷。青琛到底年少,好奇得紧,便捉著个路人问:「这客栈有什麽好玩事吗?」
路人便说:「这前几天有个戴面具的男人来了,说是帮人解决麻烦的,而且不收钱。大家将信将疑,见是不收钱,便去试试,怎知那些麻烦可真是一一给他解决了。」
「这麽神奇?」青琛讶然道。
「可不是,不过这两天突然说就不帮人了。有些人便来央告,更有些要付出千金来求他出山。」路人摇摇头,说,「有些人想硬闯,却被暗器击退,而且他还租下了三楼的所有客房,不许别人上去。」
青琛讶然道:「可知是什麽来头?」
「哪里知道!连相貌都不晓得,只知道是个男的。」路人想了想,说,「不过这位先生倒是在客房门外悬著一副对联。」
「什麽对联?」
路人稍一寻思,便说:「上联是:镜中藏日月,下联是……是……是什麽来著?」
「袖里锁乾坤。」俞无念突然说道,「是与不是?」
路人便道:「正是!这位公子怎麽知道?难道你也是像他那样的能人?」
俞无念笑道:「我哪里是能人了?只是多读了点书,知道一些名句名联罢了。」
说著,俞无念便带著青琛进了客栈,客栈的掌柜也是满头大汗,见了俞无念来,便说:「这位公子,现已客满了。」
俞无念道:「哪里是了?三楼的客房不是都空著?」
掌柜苦笑道:「公子既已知道三楼的客房空著吗,也自然知道那是因为无人可踏足三楼之故。」
俞无念笑道:「若我能踏足,掌柜能否不算我租金?」
掌柜愣了愣,道:「若你死了,我也不会给你付棺材钱。」
☆、番外·有缘千里【2】
这客栈其实也就是只有三层。那位能人便居於第三层,一个人住著。俞无念撩起袍子,缓缓地向顶层走去。许多凑热闹的都在楼梯口看著他,见此青年身量清减,似是手无缚鸡之力,如何能独闯呢?爱看热闹的众人都盯著著青年的背影看。
青琛追著俞无念,小声道:「少爷你也非爱凑热闹的人,怎麽这会儿突然想起要做这麽危险的事儿呢?您若有些什麽闪失,小的该怎麽办才好?」
俞无念一听竟失笑:「瞧你说的跟寡妇似的。你也别怕,楼上那是我的故人。他要念著旧情,那暗器飞刀一类的,也不会扎在我心口上。」
青琛呶呶嘴,说:「公子还取笑我呢!」
俞无念回头道:「你且找个地方歇著,这恐怕要费不少时间。」
青琛道:「我哪里放心得下?你们不是叙旧么?也带著青琛一旁好了。青琛在旁边伺候著不好?」
「不好。」俞无念笑道,「是否欺我没了官衔是一介草民?」
「青琛哪敢?」青琛呶嘴道,「青琛便在外头候著,要您有什麽事儿,记得喊我。」
俞无念缓缓地走到了最後一级阶梯,低头看著自己那双粗布鞋,心里竟突然有些情怯。他复又举头看有一客房,房门左右两边贴著对联:镜中藏日月,袖里锁乾坤。他就是记不得这副对联,也认得上头的字儿。
那一扇门紧紧闭著,紧得似是透不进一丝风的。他就这麽看著,胸口竟已有些发闷了。
不知是否舟车劳顿、身体吃不消,他的一双脚此刻竟无力得再迈不了一步。
俞无念紧了紧身上那件软裘,摸著软裘柔滑的皮毛,才觉得双脚暖了些,嘴巴也有了力气叫唤了:「京都故人,乞望一见。」
说完,俞无念便在外头候著。他的声音虽是不大,但也并不算很小,武功高手耳聪目明,自当能听见的。
俞无念站了一阵子,里头却也没什麽响动,他便斗胆抬起一脚,踏上了三楼的地板,却突有一片银光划过,还没反应过来,袖上便裂了一个口子。
青琛暗自心惊,意欲上前,却见俞无念举手,作了一个『别过来』的手势。他们出生入死过,只看一个手势便会意了,可青琛却还是担心。
俞无念低头看著木地板上那淋漓的血迹,又看了看自己裂开个口子的衣袖,便复抬起头,仍旧往前踏了一步。他前脚刚著地,又一片明晃晃的刀片刺在了他鞋头前,堪堪钉在地板上,却没划到他的鞋头。
青琛惊呼出声:「少爷回来吧,下回可未必有这好运气!」
俞无念只是笑笑,却依旧往前走,又来一记飞刀。他只听到耳边有破风之声,待回过神来,头上的幅巾便已裂开,头发便披散开来。
俞无念缓缓地走到门前,双手往前一推,便觉得有风拂过,脸上冻得有些僵掉了,连笑容也快挤不出来。待他回过神来,才听到青琛的尖叫声,原来他打开门的那一瞬间,便有暗器如同雨点般往俞无念身上袭来,青琛吓得不轻。
大家敛定心神,才看清散落地上的不是暗器,只是许多青绿的竹叶。但若武功够高,落叶飞花都是杀人利器,也不必非得是刀枪剑棒才可伤人。
说是竹叶也好、暗器也罢,须是看著如同密雨,却没有一点打在俞无念身上。俞无念刚刚僵掉的笑容又渐柔和,眼前是一道及地的垂帘,上面绣著暗花,看著素雅。
俞无念往前踏了一步,将门关上,隔绝了外头青琛的呼唤声。
作家的话:
=L= 这文是不是已经没人看了……因为丢淡太久了【捂面
☆、番外·有缘千里【3】
俞无念往前踏了一步,将门关上,隔绝了外头青琛的呼唤声。
「你在吗?」俞无念问道。
没有人回答他。
俞无念心里突然有些怯意:如果他不在呢?怕他不在。如果他在呢?又怕他在。
他又将软裘裹紧了一些,每年的这个时节,他都会穿起这件软裘。这件羔裘轻薄柔软又十分保暖,赠送此裘给他的人,可谓是有心了。可惜的是,那时的他却无心。
他裹紧了衣裘,才暖了些,往手心呵了几口气,便往前走了几步,伸出手指触碰那绣花的垂帘。他将帘子捞起来,便是清风扑面。他微微眯起眼睛,那熟悉的气味流转在鼻翼之间,一时间心神恍惚。
当他回过神来,看到的只是空荡荡的房间,只有窗户向他打开。也就是因为开了窗,才有清风入屋。他快步走到窗边,便看到楼下一青衣戴斗笠的身影纵马而去,挟一路清风。
这条路说长不长,他还是看清了那个人的背影。看著他如何纵马绝尘而去。这一眼,便让他想起很多事情,又让他有些高兴,又让他有些遗憾。如果能看见他的正面,那就更好了。最好的话,自然是能抱抱他,和他说说话。
他回过头走了过来,打开房门,便看到青琛一脸紧张地在等著,见俞无念开门了,才略松口气。
俞无念朝青琛招招手,说道:「你过来。」
青琛马上跳了上来,也不管会否被暗器所击。当然,放暗器的人都走了,他也自然无虞。
青琛到了房里,看著俞无念关上了门,便说:「这居然是空房子?爷的那位故人呢?」
俞无念笑笑,说:「他走了。我们在这里歇息一晚,赶明儿再追上他吧。」
青琛愣了愣,说:「爲什麽要追他?」
「因为……」俞无念犹豫了一阵,又笑笑,「反正也没别的事儿做。」
「我觉得那人挺危险的。」青琛顿了顿,又道,「而且那个必然是个高手,少爷不会武功,肯定追不上的。」
俞无念伸手要解自己的衣袍,青琛便先上前帮俞无念宽衣,又说:「您真的要追著那个人跑?」
「嗯。」俞无念说话还是那麽轻声却很坚定,「真的。」
「爷知道要往那个方向追吗?」
俞无念又是轻声答:「嗯,我知道。」
青琛将俞无念的软裘解下後搭到衣架上,看著炉子还是烧著的,便上前将窗户关上,不让风吹著了主子。看著窗户被关上了,俞无念竟觉得有些可惜,仿佛窗户外头还印著去者的身影。
青琛倒了杯茶给俞无念,说道:「你要追他追到几时?」
「追到几时都追。」俞无念接了茶杯,便喝了口,润了润喉。
青琛吃了一惊:「几时都追?一年你也追?」
「追。」俞无念答。
「十年你也追?」青琛提高了声调。
「追。」俞无念不假思索地答。
青琛叹道:「那你是追到死也要追啦?」
俞无念笑笑:「愿他别让我追到死便好。」
「小人可不懂了。」青琛瞪著眼睛说,「你这是千里追杀还是千里追夫呀?」
闻言,俞无念差点没呛著了,咳了几声。青琛忙上前顺背,说道:「都是我乱说话。」
俞无念许是呛到了,脸上有些发红,说:「行了,我自己呛著。哪能怪你。」
青琛便告退,出去跟店家为俞无念张罗吃的。心里想的是『那位故人』恐怕就是泰山上遇见的那个碧眼人。此人武功高强,出手狠辣,看著阴阳怪气又骇人,要是青琛的话,躲来还不及呢,也不知少爷为何追著他跑!
但这既是少爷的决定,青琛也不多言了。反正少爷说得也是,反正游荡江湖没事做,走这一路就当是看风景好了。
晚间,青琛与俞无念同桌吃饭。其实二人虽名为主仆,但俞无念还是没什麽架子,倒是青琛自己拘束比较多。陪侍了好久,才伺候俞无念入睡。第二天,青琛却是没俞无念早起床,竟是被俞无念唤醒的。听得俞无念轻唤几声,他忙坐起来,说:「真是该死,我赶紧起来。」
「也别急。」俞无念按住了他,说,「我帮你打水了,也叫了小二哥送饭上来,你好好洗漱,一会儿我们一起吃个早饭,然後便上路。」
青琛听了,便说:「哪能劳烦公子?」
「你呀。」俞无念笑笑,便不再说话了。
青琛洗漱过了便与俞无念胡乱吃了早饭,之後买了乾粮,准备好了才驾著马车离去。
作家的话:
突然觉得傲娇的九千岁好萌!
☆、番外·有缘千里【4】
青琛洗漱过了便与俞无念胡乱吃了早饭,之後买了乾粮,准备好了才驾著马车离去。
马车脚底飞尘的,赶得是既稳且快。每到岔口,青琛问俞无念该走哪边,俞无念必能即刻作答,确实是对去处了然於心。
青琛却觉得非常奇怪,因此就问道:「少爷的朋友是不是留下了什麽记号?」
俞无念笑笑,说:「你以为呢?」
青琛摸摸鼻子说:「我看就没有,这一路上我也没看见什麽的。再说了,这车走得这麽快,我都险些看不清路了,更何况是公子?」
俞无念又笑:「那不就是了?」
「那个人来无影去无踪的,您怎麽知道他要往哪里去啊?」
俞无念的脸色有些凝结了。
「他一定是去那儿了。」
俞无念想了很久,才沉声说道。
他们一路的赶紧干慢的,却也始终是还没到达俞无念想去的地方,也未遇见得到俞无念想见的人。
其实青琛也有些好奇,也有些焦急。事实上,青琛只见过那人一面,是在泰山一个亭林中的假山洞里头,他险些被这个人杀了。这个人戴著斗笠,斗笠上碧纱一飘,青琛只窥得那人容颜一刻。他只看到仿佛雪堆成的皮肤和墨绿得如同宝石的眼眸。
也就只是他窥得这一眼,就险些被这个人杀了。
他很想知道,这人到底是人还是鬼?这人似是心狠手辣不输江湖上的大魔头,真正是脸越白心越黑。公子怎麽会与这样的人相识呢?而且交情还似不浅。
赶了快一个月的路了,也未见到那人的踪影。虽然俞无念从无说催促之语,但青琛还是快马加鞭的赶路。青琛很知道,俞无念嘴上虽然没催促他,但少爷的心里,是很想快些见到那个人的。
赶路途中难得清閒,马儿正在低头吃草,青琛便坐在马车上,远远地看著俞无念站在河边。河水映著俞无念身上那套竹青色的衣服和半旧的软裘。他目视远方地站了好一阵子,才回过头来,对青琛说:「快到了……我想。」
青琛最後总算知道了俞无念要去哪里。俞无念要去的地方是那十分不祥的祥云峡。青琛皱起眉头,说:「这个地方有什麽好的?听说还闹鬼呢!」
俞无念笑笑,说道:「哪里听来的?」
青琛瞪大眼睛说:「难道你不知道祥云峡死人谷的事吗?有那麽多的人枉死冤死的,不化成鬼才怪!」
俞无念胸口一窒,随後却是一笑:「有鬼我也去。」
青琛上前几步,要扯住俞无念。俞无念却笑道:「你怕鬼就别来了。」
放著俞无念一人入山,青琛自然不放心,而且现在已是暮色四合,山路险峻暂且不提,那饿狼毒蛇的更是难缠。青琛忙将俞无念拉住,说道:「少爷,您听小的一句。就是有鬼也好,没有也罢,天黑上山终是不好的。」
俞无念叹了一口气,说道:「我也曾在晚上在这山走过。」
青琛听了便十分惊讶:「什麽时候的事?」
俞无念答:「多年前了。」说道这个,竟有些唏嘘,他抬头看了天上明月,又道:「那时我才十七八?」
青琛便道:「少爷胆子可真大!也不知原来少爷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倒叫人生敬了!」
俞无念却笑道:「那是因为……」
俞无念那句『因为』之後的话却没说出来,只是被一阵凌厉的风声所掩——只是倏忽间一道白影略过,青琛但觉脸上有风刮过,眼睛一闭一睁之间,俞无念已经消失无踪了!
青琛大吃一惊,忙四处跑著,又嘶声叫道:「少爷!少爷!少爷!」只是他不断向四周望去,都是山林森森,月华浩浩,莫说是人影了,连鬼影都没半个——啊,鬼影!
青琛心里打了个突——刚刚那掠过的……莫不是——鬼影吧!
这个念头让青琛从头到脚都在发冷——怎麽可能……怎麽可能真的有鬼呢?都、都是传言呀!
然而,青琛的声音已经似风中的树叶般簌簌发抖了:「少、少爷……少爷?」
回答他的只有回荡的风声。
俞无念当时只是一下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却是躺在一棵大树下。他一抬头,只见是树冠森森,斑斑驳驳地漏下了许多碎碎的月影来,让人忍不住想以双手掬住。可他终是忽视了这个看起来十分少女含情的想法。他认得这棵树的,就是在多年前,他还是十七八岁的时候,他躺倒在白骨坑,柏榆将他带离了白骨坑,带到了这里。在这里,他听了柏榆说了很多过去的事,在这棵树下的一刻钟,抵得过之前的一年两年。柏榆细细地跟他说了许多事情,陈棋瑜当时是以一种震盪又温和的心境去聆听的。
就在这棵树下,柏榆跟他很和气的说话,然後状似无情地丢下了他,一个人奋身到未知的深渊之中。
陈棋瑜身上还是披著那件发旧的软裘,只是和刚刚不同、也和那时不同——他软裘下面什麽都没穿。
衣服自然不会自己掉下来。
而陈棋瑜也没有梦游脱衣的习惯。
於是,陈棋瑜只能把身上的软裘拢紧一些,看著坐在不远处山石上的那抹白色的人影。
陈棋瑜听说过,如果你跟一个人很熟悉,那麽即使是看一眼背影,你也会认出来。
陈棋瑜现在是相信了,即使是隔了这麽多年,只是一眼背影,他就认得出来。除了国丧之时,陈棋瑜几乎没见过柏榆穿素服。九千岁衣著华丽,喜好珠光宝气,那是人尽皆知的。然而,九千岁喜欢的,柏榆却不喜欢。陈棋瑜犹记得富丽堂皇的九千岁王府上,始终保留著一间朴素乾净的睡房。在那房间睡过的,只有九千岁和陈棋瑜。
今天的月色是极好的,让陈棋瑜不禁想起十六岁那年中秋,九千岁和他赏月的那个晚上。那天的九千岁也是穿了一件很朴素的直缀,和他和气地聊了许多,只是当时陈棋瑜对九千岁太过防备、太过害怕,错过了许多值得珍视的眼神。
陈棋瑜每每想起来,都是很懊悔,懊悔当初没有好好珍惜九千岁每一个温柔的眼神。
柏榆现在就在山石上,穿著非常儒雅素净的白色长衫,宽大的广袖在夜风中如同一片白云一样飘逸,他的手上按著一枝笛,放在嘴边轻轻吹著。陈棋瑜怀疑那是笛子,又怀疑它不是。因那笛声的音质是他所没听过的,清越透彻,仿佛要穿透云层、刺破月亮一般,其音靡靡,又似是芝兰在夜中暗自吐露芬芳,随著这习习清风,能将这暗香散到千里之外。陈棋瑜这麽听著,就竟有些醉了。
陈棋瑜觉得自己已经有些不正常了,也不知是月色的缘故、笛声的缘故还是九千岁的缘故……他第一件想到的事,竟然不是要去找衣服,而是要过去看看柏榆的样子,跟他说话话,问问他这是什麽乐器、吹的又是什麽曲。
他走的步子并不故作轻缓,不时踩在沙石上,可是柏榆却似根本不知他要过来,只是依旧一派怡然地弄笛。当陈棋瑜走到柏榆身边的时候,双腿却是十分的凉了。因他刚刚躺著,虽然被剥掉了衣裤,却还是缩成一团,有毛裘裹著,旁边又有篝火烧著,不至於觉得冷。现下他已离篝火有些远了,毛裘只是堪堪遮住了上身,有半截屁股露了出来,晚风一打,不冷得哆嗦才怪。
感觉到他走近了,柏榆才慢慢将视线移到陈棋瑜身上。时隔多年,陈棋瑜终於再见到柏榆那张脸——那张依旧风神俊逸、不被年岁所改的脸,他的心中自是澎湃不已,仿佛有巨浪翻腾。
这些年,倒是陈棋瑜变得多,少年的轮廓完全褪去了,五官成熟了起来,却还是书卷气甚浓,身体也略长高了些。不过柏榆早在陈棋瑜熟睡的时候,将他由头到脚看了个遍,要说摸也摸过了,因而此刻对视倒是不那麽惊讶好奇了。
但是,当柏榆的目光落在陈棋瑜遮不住的下身时,笛子的音调还是在所难免地走偏了些,然而不过半拍,他就忙将吐息压住。
若是平日,陈棋瑜一定能听出来,只是此刻他太沉浸於重逢的惊喜中,所以也没注意这音调上的小小失误。
作家的话:
肉……快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