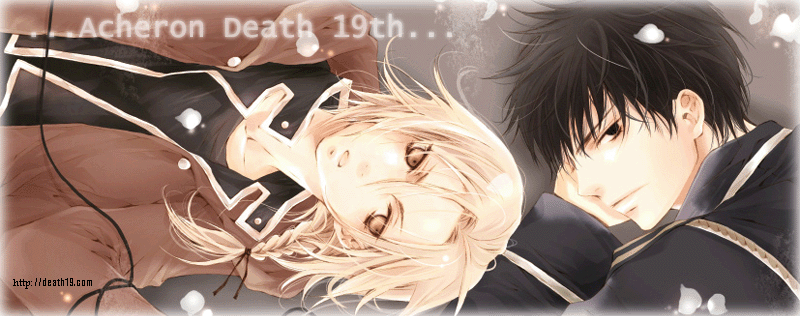番外:返京
严靖和自报上得知吴大帅兵败退隐一事时,正是几年后的冬天。
徐景同也瞧见了这个消息,正是个欲言又止的模样,又不知如何开口。严靖和索性就装着什么都不知道,又过数日,徐景同才犹犹豫豫地问道:「吴大帅如今带着小少爷回京定居了,少爷可要去瞧一瞧?」
严靖和一听,只淡淡道:「瞧什么?他这些年来都跟着岳父,恐怕也不认得我,又或者只当我死了,何必去凑这个趣……没意思。」
徐景同不以为然,「小少爷毕竟是少爷的亲生骨肉,又是一脉相承,断没有不认少爷的道理。」
「若是我去见了他,叫芳娘得知此事,她又该如何自处?」严靖和放下手上那本书,起身来到徐景同身侧,微微躬身,附在徐景同耳边道:「你不是一向最怕我跟她有什么瓜葛的么?如今怎么变得这般大方?」
徐景同神情困窘,尴尬道:「不是……」
「不是什么?你倒是说清楚。」严靖和刻意在他耳边低声道,不时用鼻尖碰一碰他耳廓,又亲了一亲,「你不说得清楚些,我可不会明白的。」
徐景同咬了咬牙,涨红了脸,小声道:「便是少爷不在乎,也得为已故的老爷想一想……」
严靖和闻言,神情一动,却是站直了身躯,皱了皱眉。这少爷的称呼,说了无数次,徐景同还是改不过来,严靖和无可奈何,只得任他去了。现下听在耳中,却忽觉这称呼刺耳极了。
徐景同犹未察觉他的异样,继续道:「便是瞧上一眼也好,吴大帅如今退隐,说不准生活上有什么麻烦,倘若小少爷亦是生活不便,那又该如何?能帮的,自然得帮上一帮,省得少爷血脉流落在外,岂不是……」
「听你的便是。」严靖和打断了他,「你想怎么样,都随你罢。只是有一事需得依我。」
「什么事?」徐景同有些困惑。
「届时到了北京再说。你要是闲着,便去订车票罢。」严靖和淡淡道。
虽是对徐景同这般说了,但说到底,严靖和却不是十分地想见自己的独生儿子。即便血脉相连,又是嫡出的独生子,然而自瑞儿出生以来,始终是由母亲照拂,后来吴氏改嫁,瑞儿便由吴大帅亲自教养,如今算来,也约莫七八岁了罢。
严靖和对这个陌生的儿子却没什么特别惦念之处,只是徐景同说得不错,到底是严家的血脉,也不知道他跟在外祖父身边,如今过得究竟如何,因此千里迢迢去看望一番,似乎也有其必要。
徐景同大约相当期待见到那个孩子,订好了车票,明明还有几日才出发,却早早就开始收拾行李,还带上了一些这年纪孩子会喜欢的玩物,瞧着倒像是个后母讨好继子的模样,叫严靖和瞧着都有些哭笑不得,又隐隐有几分不悦。那人忙着这些琐事,却忽略了自己,他虽说不上十分嫉妒,但也有几分不高兴。
出发前一晚,严靖和拉了徐景同上床,不顾对方支支吾吾,便堵住那人的唇舌。因熟谙此事,徐景同很快就反应过来,一边响应,一边含糊地劝谏道:「明日还要上火车,少爷何必如此。待到了北京再……也不迟……」
「我想要。」严靖和斩钉截铁,不容辩驳地道:「现在就要。」
其实他哪里不知道,明日要上火车,若是当真做了,只怕他们两人其中一个明日就要腰酸背疼,又如何能捱得住遥远的车程,恐怕往后几日都会身子不适。只是严靖和这会心情不大好,是以明知此事,却又刻意为难徐景同。
徐景同面有难色,迟疑半晌,方忍着羞耻道:「那……我用嘴弄……可好?」
「若能弄得我舒畅了,便放过你这一遭。」严靖和若无其事道。
徐景同手指灵巧,很快就解开他身上衣物,严靖和感到身上一凉,胯间那物事登时被含到了一个潮湿温暖的所在,叫他浑身一麻,几乎生出一丝飘飘欲仙的感觉。徐景同含得很深,不一会儿,那物事就胀大起来,变得又硬又烫,徐景同无法整个含住,只好松了口,伸出舌尖舔舐前端。
严靖和瞧着眼前光景,一时之间,却是心猿意马。
徐景同生得文秀,涨红了脸的模样本就好看,努力含着那物事时,情不自禁地蹙起了眉头,更是叫人意动……严靖和不知不觉伸出右手,抚着徐景同脸颊,故意嘲道:「就当真这么喜欢男人的这物事?」
许是此举唬了他一跳,徐景同神色一僵,半晌,才恳求道:「少爷……」
「快说。」严靖和不肯放过他。
徐景同神情窘迫,闭了闭眼,终究老老实实道:「只有少爷的,才喜……喜欢……」他忍着羞耻说出这些话来,只觉得困窘得想一头撞死。然而不知何故,在他说出这话后,严靖和却一声不吭。他感到有些奇怪,便抬头一看,登时吃了一惊。
严靖和神情古怪,彷佛意外,脸上微微泛红,「这等话你倒还真说得出来,是我小瞧你了。」
徐景同大窘,连忙道:「这不是少爷让我说的么?怎么如今又……」
「我瞧你往常是个容易害臊的,没料到你还当真说出来了。」严靖和撇唇一笑,「既是喜欢,那就劳驾你替这物事泄一泄火了罢。」
徐景同脸上通红,尴尬得无地自容,索性闭上眼,含住那物事便吸吮起来,只求能快快结束这桩差事;只是不知何故,严靖和却是久战不衰,他又舔又弄,那物事却仍硬得很,没有一丝要宣泄的模样,徐景同不由得有些沮丧。
严靖和低低喘息,又碰着徐景同的脸,哑声道:「够了。」
徐景同一怔,抬起头来。
严靖和命令道:「脱了衣服上床。」
徐景同只道他要动了真格的,不由得恳求道:「少爷……」
「叫错了。」严靖和打断了他。
徐景同一愣,从善如流地改口唤道:「平章哥哥……」
严靖和瞧着他,过了半晌,方无奈道:「我明白,只是泄火罢了。必不会叫你明日下不了床,误了火车。」
徐景同得此保证,终于松了口气,匆匆解下身上衬衣,褪尽所有衣物,爬到床上。严靖和却叫他跨坐上来,徐景同有些不解,但仍听命于人,照章行事,分开双腿,坐在严靖和两腿间。
过了一会,严靖和一手扣住他腰部,腰身一挺,那硬烫物事便生生磨蹭着他两腿之间的部位,徐景同再是愚钝也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连忙并拢了大腿,让严靖和弄得舒服些。
那物事许是得了趣,前端溢出些汁液,弄得徐景同两腿之间有些滑腻,一时又感尴尬,又是无措,又不敢打搅了严靖和的好事,只能生生忍着,并紧双腿;严靖和动作不快,彷佛还未及难耐之处,两人下身彼此磋磨着,不过片刻,徐景同便也有些动情,两腿间那物事挺得笔直,胀痛难忍。
「我左手不便,你自己弄罢。」严靖和在他耳边低声道。
「不成……」徐景同忍着呻吟,鼻息粗重混乱,急得发慌,「我不成的……」
「那该如何是好?」严靖和并不慌乱,甚至还有自问自答的余裕,「如今又不能进去你那处,要不然,弄着后头叫你丢一遭,也不是什么难事。可惜你不愿……」
徐景同当真是急了,犹豫片刻,便伸手去弄自己双腿间的物事,不过弄得几下,便一泄如注,着实是快了些。徐景同低喘着,臊得满脸通红,便听严靖和奇道:「竟这般快?只不过旱了数日……」
他忍着羞耻,不敢再听下去,横竖如今也是任人摆布了,索性大着胆子,抬头去亲严靖和,好让那人别继续说出这等荤话。严靖和陡然被亲,虽有几分意外,但也不曾拒绝,被徐景同亲了又亲,终是不再刻意以言语逗弄他。
过不多时,严靖和也宣泄而出,弄得徐景同两腿间一片潮湿,两人搂在一处,一时谁也不想动弹。好半晌,徐景同回过神来,动了动身躯,轻声道:「让我起来……」
「别动。」严靖和只抱着他,不耐地道,「你就不能让我歇一会么。」
「少爷自歇着,我去弄些热水来。」徐景同一贯老实,又是个好脾气,也不生气,柔声道:「身上汗湿,若是不快些弄干,只恐要着凉。」
「别瞎忙了,你陪我歇着便是。」严靖和不以为然。
「可……」徐景同还想再说。
然而严靖和已经紧紧地抱住了他,将脸埋在他怀中,看起来倒是个不肯放手的架势,徐景同心道稀奇,这人这般模样甚是少见,令他无端生出几分微妙的情绪,一边在严靖和背脊上给猫顺毛似地拍抚了几下,严靖和便动了一下,原先靠在他怀中的脸愈发埋得深了些。
这是……撒娇么?
徐景同感到有些好笑,又思及明日之事,只当严靖和是在为即将返京与儿子见面而生出几分紧张无措,倒也不觉得奇怪,只是搂着人,待严靖和终于肯松手之后,才起身去弄了热水,将彼此身躯都擦拭干净不提。
翌日早上,严靖和同徐景同乘上了火车,启程前往北京。
抵达目的地后,严靖和本想去寻一间旅店暂且住下,不料徐景同却带着他到了一处不大的四合院,瞧着半新不旧,一片青瓦灰墙,便如寻常百姓的住家。严靖和看了一看,问道:「这是你的宅子?」
徐景同点了点头,拿钥匙开了门,「早先置办的,我还以为不会有机会来这里……」
严靖和闻言,心中难免起了疑窦。早先?究竟是早到了什么时候,莫非是当年他战败之前?想归想,只是表面上仍做出一副没事人的模样,淡淡道:「你什么时候有了置办宅子的念头,我竟不知道。」
徐景同放下手上皮箱,有些迟疑,终究道:「当年……少爷与夫人即将成亲,我又不明白夫人是怎样的性子,只想为自己留个退路,是以拿少爷当初赏的买命钱,挪了一部份置办了宅子。」
严靖和一怔,「你怕被赶出去么?」
他听闻此言,心中却是一涩。他当时对徐景同已是隐隐有几分感情,只是说不出口,自己也不大明白,再有就是,父亲遗命始终刻在他心上,他与吴氏订亲,也是存着成家立业,为严氏开枝散叶的心思。便是他一心想着徐景同,这事也不可能抛下的,何况他当时什么也说不出口。
徐景同有些尴尬,辩解道:「不是怕被赶出去……」顿了一顿,又彷佛下定了决心一般,老实道:「我当时想,往后府中有夫人操持,我只怕是待不久的,不如先置了宅子,往后若是娶了媳妇,便有现成的宅子可住,倒也便宜……况且,我并不明白夫人是什么样的人,恐怕她容不得我……」
严靖和听到此处,打断了他,「到头来,这宅子可没派上用场。」
「你说得是……」徐景同若有所思地应道,也不说话了。
徐景同领着严靖和进门,四合院内冷冷清清,屋内只有几样必备的家具,因久无人来,满是尘埃,严靖和一进门便打了个喷嚏,徐景同连忙道:「少爷自去外头歇着,我把屋子清扫一番。」
严靖和在这种事上是不会与他争执的,横竖一只手都废了,省得给他添了麻烦,索性便在院子里站着,瞧徐景同打理卧房;因只打算住上几日,徐景同便仅仅打理了东边的卧室同厢房,其余几间倒是放着不管了。
等到他打理好了,外头早已夜色深暗,严靖和到胡同外头买了些吃食回来,徐景同煮了一壶热茶,两人就着茶吃着热腾腾的肉包子,算是勉强对付了一餐。
晚上,两人烧了些热水,草草洗过澡后,躺在床上,徐景同正想问何时去拜会吴大帅同严小少爷,便听严靖和道:「明日你拿了芳娘先前留给你的玉佩,自去见岳父,替我把支票捎给瑞儿,不过别说是我给的,只说是我过世后留给他的。」
徐景同一脸愕然,「少爷连小少爷一面都不肯见么?」
「见与不见,又能如何。」严靖和淡淡道,「我一日都不曾教养过他,哪里有脸面要他认我这个老子。」
「话不是这么说的。」徐景同难得地反驳道,「虽说不曾教养过他,但小少爷许是记挂着少爷也说不准……」
「别说了,明日你自去罢。别泄漏了我的行踪。」严靖和顿了顿,「往后的,再看看罢,反正还要在京中待上几日。」
徐景同只得应允,再没开口劝他。
瞧他那副欲言又止的模样,严靖和却感到有几分好笑。
时至今日,他对父子亲情也不抱什么期望了,一日都不曾养过,恐怕瑞儿也不记得自己这个爹了,纵是记得,恐怕吴大帅也如当初跟芳娘说的一般,只道他是死了。
这样一来,严靖和又凭什么去说自己尚且活着呢?既然活着,又为何几年来都避不见面?往后改嫁的芳娘又该如何自处?是以严靖和一开始便打定了主意,仅让徐景同出面,自己不去见儿子。
身旁那人在床上翻来覆去,彷佛夜不成眠,严靖和一手按着他,问道:「你这又是怎么了?」
徐景同沉默半晌,方怅然若失道:「若是我爹仍活着,又不肯来见我,我定然会恨他的。」
他这样说话,显是要说些心里话了。严靖和暗道稀奇,面上却不动声色,平静道:「这话从何说起?」
「我幼时家贫,爹娘早逝,只怕是我娘去得更早些,我记不得她长什么样子了,不过倒还记得爹的模样。」徐景同顿了一顿,「他长得同我不像,是个高大的汉子,对我也是极好的,家里穷得什么都没了,他还肯省出一点钱,买糖与我吃。」
严靖和一声不吭,默默把人揽到自己怀中,紧紧抱着。
徐景同彷佛受到了鼓舞一般,又继续道:「后来我爹病了,家中生计艰难,不得已把我托给亲戚抚养,没过多久,他便去了……我在亲戚家里帮工,吃不饱穿不暖,后来长大了些,才被卖入府中。如今想来,也不知道爹被葬在何处,那几个亲戚也早就不知所踪,始终寻不着人……」
严靖和沉默半晌,低声道:「若是要寻,也得有些门路,如果你想……」
「不必了。」徐景同极难得地打断了他,叹道:「都这么多年了……只怕是寻不着了。我只想说,少爷若是不去见小少爷,说不准会抱憾终身……如今这样的时代,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打仗,没几个平和日子,我……」
「别说了。」严靖和打断他,沉声道:「让我再想一想。」
徐景同低低应了一声,也不说话了。
隔日早上,严靖和一夜未眠,瞧着有几分憔悴,只让徐景同自去吴府拜会,徐景同心知劝不得他,便自个儿出门了。严靖和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不到正午,徐景同便回来了。
严靖和犯了懒,也不起身,便听那脚步声往卧房走了过来,徐景同进门后,来到床沿坐下,小心翼翼道:「少爷这是怎么了?还困着么?」
他摇了摇头,道:「说罢,今日去吴府,情况如何?」
「没见到小少爷。」徐景同顿了下,斟酌着道:「吴大帅昨日恰巧带着小少爷出门了,那边的管家说是要等到后日才会回来。」
严靖和并不答话,也不知道心底究竟是松了口气,还是有些失落。他表面上只做无事,淡淡道:「既然不在,那也罢了。后天再去一趟也不迟,这两日便歇着罢,许久没在此地待着了,下午出去走一走。」
徐景同倒不反对,又道:「如今是正午,不如出门去吃午饭?」
严靖和起身,换了一身齐整衣服,便与徐景同一起出门了。
走出胡同口,外头倒是热闹,严靖和与徐景同一合计,随意寻了家小店坐下,点了两份汤面,又要了些小菜,幸而滋味倒也不差。吃过饭后,两人在街上走着,严靖和心中既有几分陌生,又有些许怀念。
他曾在北京住的时间不算长,但好歹也有几年时光,路过一处,他感到有些熟悉,忽然想起,那是从前去过的一家洋人餐厅,彼时严靖和与吴小姐来此地约会,又偏偏叫徐景同跟着,想看他是否会喝醋……现在想来,那都是许久以前的事情了,模糊得如同上辈子发生的一般。
「少爷?」徐景同唤了一声。
严靖和回过神来,听出那嗓音中的一丝惦念,便回过头,撇唇一笑,「怎么了?」
「没什么。」徐景同神情有些微妙,「少爷可是想去那里用餐么?」
「不。」严靖和停顿了一下,道:「难得回北京城一趟,自然要多尝一些上海没有的吃食,租界内最多这种洋人餐厅,你至今还没腻味么?」
徐景同只是好脾气地一笑,「少爷吃什么,我便吃什么,说不上腻味。」
两人沿着街道走着,严靖和往日不大有机会在街上行走,徐景同跟在他身旁,到了傍晚,才买了些吃食,回到徐景同那个小小的四合院。因着实饿了,徐景同买了半只烤鸭,又买了几个菜,两人吃过晚餐,又歇息片刻,便去洗澡。
徐景同烧了热水倒到浴桶里,严靖和不愿他忙碌于此,便开口要徐景同脱了衣物一起洗。徐景同按着他的话,脱了衣物跨进浴桶,两人挤在一起,却别有几分趣味。严靖和眼尖,瞧着徐景同那副困窘模样,便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又拿脚掌去揉他两腿间,弄得徐景同尴尬不已,满面通红。
徐景同忍无可忍道:「少爷再弄下去,我可当真忍不住了……」
「谁要你忍了。」严靖和不以为然,理直气壮,「横竖后天才要去见人,你不理会我,叫我如何打发时间?」
「若是我在上,少爷也愿意么?」徐景同小心翼翼问道。
「都这么多次了,你何苦每回都要问,倒像是我刻意不许你一般。」严靖和没好气道。
「不是这个意思!」徐景同慌忙辩解道,「我只是……我……我……」他说到此节,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一脸急切窘迫,又不知道如何解释,慌得手足无措。
严靖和本就不是当真指责他,这会便按住他的手,沉声道:「不是就好。这些年来,我俩一起过日子,怕是委屈了你……若你忘了,我再说一次,你叫我一声兄长,我自然只有把你当亲弟弟一般疼惜的。」他说着一顿,撇唇笑了,「只这床上的事情,始终不能放过了你,便委屈你忍着罢。」
「平章哥哥不必如此……」徐景同连忙道,「那床上的事……我也喜欢的!」说完,他脸上泛红,又鼓起勇气望着严靖和。
严靖和哪里还有别的话说,压着他后脑杓,直接亲了过去。
徐景同发出一声情不自禁的喘息,两人浸在暖洋洋的热水中,过了一会,水渐渐凉了,严靖和便起身,随手拿换下的衣物擦干身子,便把人拖到床上,两人在床上滚了一圈,双腿交缠在一处,气息粗重,严靖和才想开口,就被徐景同的动作唬了一跳。
此刻不比往常,徐景同胆子大了,便拿着膏脂,用手指蘸了一些,去弄他身后那不可告人之处,彼此那物事都已经硬了起来,相互磨蹭,严靖和也懒得折腾,索性让徐景同弄着,自己一手勾着他颈项,去亲他嘴唇。
徐景同脸上红得异常,彷佛要滴出血一般,神色沉迷又紧张,严靖和最爱瞧他这副模样,在他脸上亲了又亲,忽地低声道:「别弄了,直接来罢。」
「不成!」徐景同却在此时显出了几分难得的坚持,「上回也是这么说的,结果竟伤了少爷……」
「我等不及了。」严靖和有心为难人,又故意去撩拨他。
这种情形下,亏得徐景同有那般定力,竟当真忍住了,决心要等弄得严靖和适应了才肯进去。严靖和忍着疼,待徐景同当真全根没入后,便刻意附在他耳边,戏弄地说些荤话,诸如「当真硬极了」或者「丢在里头也无妨」,闹得徐景同连颈项都红了一片,窘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徐景同忍着一丝泄意,挺动腰身,严靖和顿时不吭声了。
细细去看,才看出了那张脸上泛着红潮,目光像是浸在水中一样,叫人舍不得挪开视线,一看再看,也不觉得厌倦。严靖和偶尔低喘了一声,徐景同便放轻了力道,只怕伤着了那人,到了后来,却是连分毫顾忌的余力都没有了,只记得严靖和拥紧了他,竟是如获至宝一般,从头到尾都不肯松开手。
不知何故,徐景同却感到有些想哭,只是强忍着不愿失态罢了。
隔日,两人几乎没下过床,横竖也没事,徐景同又向来顺着严靖和,是以往后之事亦是可想而知。徐景同心知严靖和不愿去见儿子,但也并不放弃,多少劝了几句,只是严靖和听是听了,却总是随口敷衍过去,显是对此事提不起兴致。
一转眼,便到了后日,徐景同别无办法,只得独自前往吴府拜会。
严靖和独自待在这四合院中,忽然思及些许幼时琐事,不知何故,隐约有了几分怅然若失的心绪。他自幼便失了娘亲,对那个身为父亲妾室的娘也没什么记忆了,只记得彷佛是个长得相当好看的女子,只是生来多病,成日躺在床上养病。
后来娘亲抱病去了,他便是由父亲独自养着的,当时父亲想是怕府中妾室慢待了他,不仅亲自教养,一应物事都是最好的,他要什么,就有什么,府中下人除了爹以外,便以他马首是瞻,纵是最受宠的姨太太也不敢在他面前说一句硬话,生怕得罪了他,便要开罪于大帅。
严靖和幼时脾气不好,气极了便拿马鞭抽人,后来年纪渐长,虽是稍微收敛了些许,但仍算不得好性子,府中下人在他身旁都待不长,他嫌那些人不好,便一个又一个的换人,父亲也容着他,这点是谁都知道的,后来跟在他身旁的徐景同大抵是被管家告诫过了,分外的谨慎,虽是笨了些,但却老实得很。
他不喜欢自作聪明的人,也不喜欢处事圆滑的人,就喜欢老实人。是以徐景同这个老实性子,虽不够聪明伶俐,但到底还是合了他的性子。
父亲待他,确实是宠得过度,让他这样一再换着仆人,又许他这样随性恣意,并不是谁都能作到的;况且他父亲又是个堂堂的督军,但对着严靖和却不大摆出那些架子,严靖和每每驳他的话,他父亲也不动怒,只是随他高兴,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眼下想来,却是他这个作儿子的不是。
虽是成家立业,有了后嗣,但独子却是旁人养着;前些年兵败,又被软禁数年,至今都不曾东山再起,父亲留下的军队散得干干净净,什么也不剩,便是手上还有几分产业家底,到底也只是衣食无缺罢了。
严靖和想到这里,却是有几分心酸。
他不能去见自己的儿子,自然也不能叫儿子回湖北老家一趟,到宗祠里向祖父磕几个头,纵是他爹不怨他,严靖和也多少有些怨着自己。只是这话却不能说与徐景同听,否则恐怕徐景同便要一心忧虑着此事。
便在这时,严靖和听到外头传来脚步声,想是徐景同回来了。听见门扇被推开的声响,他回过头,正想问徐景同情况如何,便怔住了。
徐景同确实是回来了,只是身旁还跟着一个长相极为熟悉的孩子,严靖和全然愣住了,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能说些什么,仅仅是瞪着那个孩子,失声道:「这是怎么回事!」
那孩子不作声,好奇地望着严靖和。
徐景同犹豫片刻,终是小心翼翼道:「少爷不必忧心,这是吴大帅答允的,少爷与小少爷毕竟是骨肉血亲,没有到了此地又不让他过来拜见的道理。只是此事万万需得瞒着吴小姐,不能令少爷上门,是以才令我带着小少爷回来拜会……」
严靖和沉默半晌,沉沉道:「你如今倒是懂得自作主张。若是你不说,岳父怎么会知道我在此处。」
徐景同这回却没有认错,反而老老实实道:「我自作主张,自然有我的不是,过后再请少爷责罚。」他又顿了一下,想到了什么,匆匆道:「我去煮水泡茶,请少爷稍等。」说完,竟匆匆离开厢房,刻意将这对父子单独留在此处。
这人胆子愈发大了,简直是胆大包天。严靖和恨恨想道,又瞧了一眼那孩子,那孩子亦平静地瞧着他,一时之间,两人陷入了某种难以言喻的寂静氛围中,谁也不说话,谁也不曾转身走开。严靖和察觉到这孩子生得与自己幼时的样子一模一样时,心中涌出了一股复杂的感受。
他迟疑片刻,便听那孩子道:「爹?」
只听这一句话,严靖和忽然觉得心头一软,再有什么严苛刻薄的话都说不出来,也忘了要训斥徐景同一事。他定定瞧着这孩子,终是叹了口气,而后问起一些家长里短的琐事,诸如回京后日子过得如何、外祖父身子可还硬朗、如今读什么书一类之事,那孩子也不惧他,瞧着是受过正经教养的,毫不怯场,嗓音清脆地一一答了。
严靖和听着他的话,明白吴大帅虽是退隐,但回京后也还有一些权势,亦有几个故旧,祖孙俩日子过得不差,倒也放下了心。
不知过了多久,外头有人敲了敲门,却是吴府的管家来接人了。严靖和嘱咐儿子要认真读书,又说有事可来上海顺兴洋行寻他,接着便让人离开了。又过片刻,徐景同才慢吞吞地回到东厢房内。
严靖和瞧见他,淡淡道:「你不是去泡茶了么?茶呢?」
徐景同一怔,道:「我忘了,茶叶没了。」
「说罢,你究竟为何这般自作主张?」严靖和沉声道。
徐景同答非所问,「少爷才是……见了小少爷,当真一点都不欢喜么?」
严靖和难得语塞,片刻后,恼怒道:「好,好极了,你的胆子竟这般大。我都说了不见他,你还能阳奉阴违……」
徐景同认真道:「我如今又不是下人,自然不奉少爷命令行事。」
严靖和被他这么一噎,却是当真说不出话了。
「此番是我自作主张,纵是少爷恼恨也罢,我实是顾不得了。」徐景同老实道,「只是见上一面,不碍什么事的,况且吴大帅也是允的,少爷不必恼怒,否则怒气郁积于心,恐怕伤了身子。」
严靖和一声不吭,也不瞧他,过了一会儿,终于无可奈何道:「你从未为人父母,到底是不明白的。」
徐景同奇道:「少爷这话是什么意思?」
「若是不得见也就罢了,不想就没事了,横竖他有外祖父照拂着,往后出不了什么岔子。」严靖和语气淡然,若有所失,「如今你迫我见了他,叫我如何能放得下他。我心里原本只挂念着你一个人,今后又要添上他了……」
「可是有什么不妥之处?」徐景同仍旧不明白。
严靖和慢慢道:「他生得这般像我,偏偏是岳父养着的,往后还要支撑岳父家业,方才我问过了,岳父要他以后成亲,令次子改姓吴,以承继吴氏香火,我的生死又得瞒着芳娘,同他一辈子都不能父子团聚,纵是见了一面,也不过平添一分不能实现的念想罢了。你说,这有什么好的?」
徐景同一愣,方懊悔道:「是我错了。」
「不怨你。」严靖和叹息,「横竖见也见了,也没什么不好。」他顿了一顿,低声道:「确实生得极像我……」
徐景同没有说话,只是走了过去,靠在严靖和身侧。
过了一会,他换了个话题道:「少爷幼时也是这个样子的,只是小少爷是个脾气好的,不大会高声说话……」
严靖和一笑,「你这是在指摘我了?反正我是个脾气不好的,动不动就打人。」
「少爷那时候极是吓人……府中下人都怕极了,又不敢宣之于口。」徐景同颇感怀念,若有所思,「少爷虽是脾气不好,不过只要老老实实的,少爷便不大会动怒……」
「不必说得这般委婉,我是什么性子,我自己清楚得很。」严靖和不留情面地打断了他,「若你是个不老实的,那时万万不会拖你上床,往后自也不叫你服侍,你我便如寻常主仆一般,各行其是罢了。」
徐景同沉默片刻,忽然问道:「少爷那时为何独独找了我?」
严靖和有些诧异,道:「问这个做什么。」
「我生得又不好看,也不是个懂得讨好人的……」徐景同彷佛有些忐忑不安。
严靖和听到这里,却是笑了,「我那时瞧见你哭了。」
徐景同一愣。
严靖和也不理会他,继续道:「你打破了物事,遭管家骂了一顿,便躲起来一个人哭。我那时瞧见你哭,说不出缘由,便想让你哭得狠些……」他笑了起来,倒像是有些开怀,「你那时是第一次,又怕又羞,后来还疼得哭了,瞧着挺招人的。」
徐景同脸上发烫,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现下想想,那时弄得你那般疼,却是我的不是。」严靖和笑着道。
徐景同摇了摇头,又不明白该如何回应,只好道:「不怪少爷的。再说,后来……便好些了……」他垂着头,脸上泛红却不自知。
严靖和瞧着他,只觉得方才的郁闷都消散了,情不自禁道:「自然得怨我的。往后必不会再叫你疼着。」
徐景同尴尬不已,讷讷应声。
严靖和笑了一笑,不再逗他,瞧向窗外,说不出为什么,却是满心的宁和平静。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