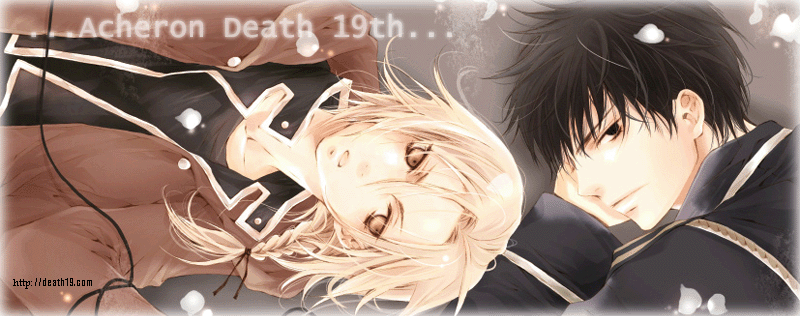番外二 长明
1.
二十岁至二十八岁,章决曽路过森那雪山两次。
一次独身一人,一次和Harrison同行,但都在冬季,大雪封山,理所当然地没再往上爬。
那时章决活得混沌自由,时间很多,当然也有别的机会能去,只是无法坦然面对自己的自作多情,因此不敢上山。
婚后,章决并不是一直在家,他和陈泊桥一起去了一些地方,准备了迎接新生儿的各种用品。
夜晚陈泊桥常常带章决在庄园里散步,他和章决聊了不少幼年的事,有时说自己在连廊奔跑,老管家在后头也追着他跑,有时谈父母的冷战,谈搬去欧洲后的生活,说起父亲给他打的短电话,和深夜在瑞士的孤堡里穿着睡袍游荡的母亲。
谈话的最后,陈泊桥总在芬芳的蔷薇丛旁亲吻章决。
他绅士地低头,与章决对望,草丛间一盏盏隔得很远的落地灯,温和地照射着亚联盟的空气与水汽。
也有些晚上,陈泊桥的继母会带着礼物来看望章决。
她是一位灵巧美丽的妇人,有很漂亮的一双眼睛,在得知孩子性别后,继母买了许多可爱的男婴连体衣。章决的父母也来住过一段时间,与陈泊桥相处融洽。
二十九岁时,章决和陈泊桥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或许是因为怀孕的时的检查都不差,一切都显得平静和安详,章决和陈泊桥都以为这次会很顺利,直到诞子第十二个小时的凌晨,章决被腹部剧烈的疼痛催醒,而压在他手上的血压测试仪开始闪灯报警。
下一秒,房门被人推开,章决昏沉地疼着,眼睛很快不能视物,脑中只留下了似是而非的陈泊桥和医生的残影。
他昏迷了五天,输了两千毫升的血,醒来时第一眼看见的人是陈泊桥。
那天下午章决的脑袋转得很慢,努力地分辨陈泊桥的样子。
陈泊桥还是体面地穿着整齐的衬衫,没有胡茬满面,也没有欣喜若狂,只是在与章决对视时,眼底盖不住的血丝和紧闭的唇,让章决下意识得觉得心疼和心酸。
“章决,”陈泊桥笃定地对章决说,“你醒了。”好像真的胸有成竹,知道章决一定会没事,会醒过来一样。
章决想说些什么,或点点头,但陈泊桥握着他的手心,俯下身来,用嘴唇贴住了他的额头。
陈泊桥的嘴唇很冰,手也没什么温度,身上的信息素味道淡得几乎无法察觉,他吻章决吻得太久了,久到章决的父母和护士走进来,站在不远处,却不敢走近。
最后陈泊桥起身,是因为听见婴儿哭了。
婴儿的哭声很细,断断续续地,叫了几声,又安静了。陈泊桥按了病床的电动控制器,让章决慢慢坐起来,章决的背抵着床褥,转过眼去找在他的生**里暂居过的小生命。
小生命睡在一个椭圆形的、有些倾角的、高高的透明床里,由章决的母亲看护。他小小的手脚被裹在薄薄的浅蓝色包衣里,一下一下轻轻地动着。
章决看不见他的脸,眼睛一直向那儿望,陈泊桥便走过去,接过母亲手里的婴儿车,推到章决的病床旁,又把躯体还很柔软的婴儿托起来,放到了章决的手臂胖。
章决手背上还扎着针在挂水,另一只手也无力动弹,陈泊桥就轻拿着章决的手腕,让章决的指腹碰了碰婴儿的脸颊。
婴儿的面颊很柔软,带着一股软乎乎毛茸茸的热意,他眼睛睁开了几秒,又闭了起来。
章决弯了一下唇角,陈泊桥也对章决笑了。章决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有见过陈泊桥这样的笑容,开朗,松弛,温柔专注,心无杂念,像是在说他其实真的很喜欢章决,并不比章决少多少,虽然他从来没有说出口。
新生儿要洗澡,陈泊桥推着他出去了一会儿,给章决和父母留了一些时间。
章决的父母看起来比陈泊桥都要狼狈一些,但并没有说什么丧气的话,母亲也吻了章决的面颊,说“我觉得宝宝像泊桥多一点”。
父亲则说“新生儿看得出什么像谁”。
两人悄声争辩了几句,陈泊桥推着洗完澡的孩子进来时,讨论就中止了。
2.
章决出院后过了一段时间,陈泊桥动了一个手术。
他没和章决商量,在手术后的夜里告诉了章决。
章决正在婴儿床边坐着看书,陈泊桥先让育儿师先出去,然后说了自己动的那个手术。章决几乎以为自己幻听。
这项手术虽然不大,但几乎没有alpha会去做。当今的避孕手段很多,Omega的皮下植入避孕手术已经很成熟,植入后怀孕几率微乎其微,即使陈泊桥不想再要孩子,也并不需要手术避孕。
而且大部分alpha心理上无法接受这项手术,都很抗拒。
章决想说没必要,但看着陈泊桥,想了许久,才想到委婉一些的语句:“我植入避孕更简单。”
婴儿很轻地呼吸着,用腿把盖毯蹬开了,陈泊桥帮他重新盖好了,才对章决说:“你就别折腾了。”
章决申辩:“我没折腾。”
陈泊桥抬手,碰着章决的下巴,拇指很轻的摩挲着,又沿着颈部的线条,滑到章决耳后,滑到腺体边。
“你还不折腾,”陈泊桥低声笑他,“不是跟你说了,疤没什么。”
章决下周去做后颈腺体的祛疤手术,陈泊桥不太赞成他做,但章决的意志很强烈,因此最后妥协的是陈泊桥。
“我不想留着。”章决垂着头说。
他等了一会儿,陈泊桥伸手勾着他的下巴,要他抬头,看了章决一会儿,才垂头将唇印在章决的双唇,说:“随你。”
他们吻了少时,陈泊桥把章决从椅子上拉起来,离开了房间。
站在婴儿房门口的育儿师又走了进去,而陈泊桥与章决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诞子后,陈泊桥并没有再和章决做过爱,只是入眠时总是将章决抱得很紧,要十指相扣,要身体贴紧,仿佛他也曽惧怕过失去。
3.
这一次爬雪山是在章决计划之中,但旅伴在他计划之外。
接到Harrison电话时他在新独立国省亲,Harrison说很久不见他,问他愿不愿意一道再上一次雪山。孩子来新独立国后,章决父母的注意力都转移了,他正觉得自己在家已经有点多余,便和陈泊桥商量了一下,答应了。
没想到到了泰独立国,Harrison突然没空了。
他匆匆忙忙地给章决打了个电话,说有急事,挂下之后,陈泊桥的电话也来了。
陈泊桥说自己凑出了几天的假期,可以来陪他,打完电话的下午,陈泊桥就到了。
他们在泰独立国边境驱车三小时,到了森那雪山附近,导游坐在前座,犹豫地回头看陈泊桥。
“很少有人选在十月底爬山,”导游说,他的脸晒得黝黑,雀斑长在其间,泛着属于高原的光,“陈先生,您确定要爬山吗。”
“前几天山顶才下过一场雪。”司机也插嘴道。
陈泊桥坐在章决身边,章决没有发表意见,陈泊桥也不说话。
他们的车沿着环山路往上,到了登山点,两人下了车。
陈泊桥让司机开后备箱,将登山的用具和包取出来,地上的草丛里确还有薄薄的一层积雪,再网上看,是森那雪山皑皑的厚重的白,他替章决戴上了护目镜,把手套严严实实地扣好,持杖从山腰往上走。
章决以前很喜欢登山,像是到了精疲力竭的那一刻,在肌肉极尽酸楚时,他才能觉得自己真正活着。
他攀上很多高山,森那是最特殊的一座。章决在森那留过愿望,贡了一盏没想过会贡的灯。在二十九岁的末尾回想,便觉得当时的自己过得仿若夏日池塘中的蜉蝣,睁眼闭眼,暮死朝生,都没有很大的感觉。
而今章决和陈泊桥沉默着攀高,将路边的登山客从熙熙攘攘,变得零零落落,最后只剩下他们,拄着登山杖一刻不停地疾行。
章决觉得陈泊桥或许已经照顾着自己,放慢了速度,但两人体力不同,章决还是有些跟不上陈泊桥的脚步,呼吸渐渐重了,后颈有些微汗,双腿机械性地向上。
陈泊桥又走慢了些,不时拉他一把。
傍晚时分,他们终于看见了森那山顶寺庙点起的灯,一盏盏地隐在木栏和雪间。
“上次是和Harrison一块儿来的?”陈泊桥停了下来,侧过脸问章决。
他没戴面罩,只戴了纯黑的护目镜,下颌和嘴唇的线条分明,肤色健康,有一种充满生气的英俊。
冷的空气从面罩外往里挤,像碎冰一样钻进章决鼻腔,进到肺里又重回温热。
章决看着他,停顿了两秒,说“是”。
“我还没去过,你陪我进一次。”陈泊桥说。
又爬了二十分钟,他们走上了往寺庙去的石板路。
章决觉得和陈泊桥一起上山,比和Harrison上山来得更快一些。或许是因为陈泊桥在他心里更可靠,只要跟着走就好了,什么都不用想,一眨眼就到了。
有僧人在寺庙门口扫雪,看见章决和陈泊桥,微微颔首,让了让道。
进寺后,他们在大殿旁的木凳上稍稍休息了少时,章决靠着椅背一动不动,陈泊桥便拉着他的手,替他摘了手套和护目镜,放进包里,递水给章决喝。
“听说有个长明灯池,”陈泊桥看着不远处闪着光的巨大佛像,自然地对章决说,“可以去贡几盏。”
章决脸立刻热了一下,他想不起当时Harrison有没有提灯的事,想蒙混过关,便对陈泊桥说“别贡了”,又说:“拜一下就好了。”
“是吗,”陈泊桥的尾音拖长了些,他靠近少许,垂眼看着章决,抬手将章决额前的碎发往后拨,“你不是连路边的佛牌都要买么,长明灯怎么不贡。”
章决看着陈泊桥,觉得好像瞒不过去,才对陈泊桥坦白:“我贡过了。”
“也有你的。”他说得很轻,也很不好意思,毕竟确实,二十岁的陈泊桥轮不到他贡灯。
“是吗,”陈泊桥没有露出意外的表情,他对章决说,“什么时候的事?”
章决说了一个年份,陈泊桥就对他笑了笑。并不是什么嘲笑的神情,只是好像很高兴,他说“这么喜欢我啊”,搂着章决的背,轻轻贴近了,又扣紧章决的五指,拉着章决站起来,往长明灯池去。
池子里一片灯海,茫茫水面上漂浮着一盏又一盏的灯。
比章决上一次来多了很多盏,密密地互相挤撞着,盈盈火光在水上明明暗暗地闪烁。陈泊桥带着章决一道写了儿子的名字,再贡了一盏,然后便要僧人替他找寻了许久的属于他自己的那一盏。
他和章决的灯分隔在灯池两个角落,好像毫无关联,看不出是同一个人贡的,陈泊桥便要僧人将他那一盏挪一挪。
僧人把写了陈泊桥名字的灯钩了上来,章决写的那三个字,好好地封存在鎏金玻璃盒里。
陈泊桥这三个字,章决写得有些潦草,但笔画之间又界限分明,一看字迹,便能想出写字的人必定是反复地犹疑过,才最终将整个名字写到纸上。
“写得不错,”陈泊桥看了一眼,和章决玩笑,说,“是不是经常偷偷写。”
章决看着僧人把长明灯放到了陈泊桥要放的地方,才说:“没有。”
他的确只写过一次,用手指在桌子和纸上描摹了很多遍,但始终没用笔写,有时下笔写一划,就不再继续往下写。
那时总觉得是不应该的。
陈泊桥没有再说话,他说:“我订了寺后的一栋小屋子,不远,但得再走一会儿。”
他们在寺里又走了走,便向陈泊桥订的地方出发了。
4.
陈泊桥订的还真是一间很小的屋子,供夜宿山顶的登山旅人居住的那种。
屋子分上下两层,加起来只得五六十平米。底层是玄关和一间小起居室,还有简单的做饭的小台子,从窄楼梯走上楼,二层摆着一张矮床,角落隔出一间浴室。
炉罩旁放着两份未拆封的速食,章决许久不登山,今天累坏了,先上楼洗了澡。
换了睡衣下楼,陈泊桥热好了饭,放在茶几上。不知为什么,章决也不觉得很饿,他窝在沙发里,拿叉子吃陈泊桥做的意大利面,吃了几口就放下了。
陈泊桥见他不吃只躺着,就给他开了电视,播一部自然纪录片,章决看了少时,意识变得昏沉,抱着枕头睡着了。
章决做了一个近乎静止的梦,梦里的他是一个漂浮在半空的魂灵,耳畔全是模模糊糊挤过来的诵经与钟鸣,而肉身跪在长明灯的池边,垂着头许愿。
在杂乱的声音里,章决听见了肉身的愿望,于是他知道他梦见了二十来岁的自己。
陈泊桥没问,他也没说,可是梦境不会作伪,替他回溯过往,重听一次愿望。
那时他想要陈泊桥平安健康,长命百岁。
好像太简单了,也不浪漫,但这都是章决以为自己不会拥有的东西,因此希望至少陈泊桥能有。
梦被一阵轻微的触碰打断了。
章决迷惑地睁眼,发现陈泊桥正低头看着自己。
“很晚了,”陈泊桥低声对他说,“你睡了三个小时。”
章决后知后觉地注意到陈泊桥也换上了睡袍,而纪录片也早已播完,电视的屏幕按了。
雪山上很冷,不过许因为小屋面积不大,屋里的暖气很热。
章决看着陈泊桥近在咫尺的脸,也不知是怎么了,心里腾起一些莫名的酸楚,伸手很轻地勾着陈泊桥的脖子,又犹疑着不敢使劲。
“怎么了?”陈泊桥很温柔地对他笑了笑,问。
章决没说话,陈泊桥就靠近了吻他。
嘴唇相触的时候,章决闻到了陈泊桥的信息素气味,松香和沐浴液的草木香混在一块儿,一开始不那么容易察觉,但吻得久了,便愈发难以忽略。
陈泊桥半跪在沙发边,手牢牢地扣着章决的腰,将章决的睡袍扯散了,沿着章决的下巴往下,埋在章决胸口,舔吻他的乳粒,用牙齿轻磨。
他晚上没有剃须,下巴的胡茬有些粗糙,擦刮着章决肋骨的凸起。陈泊桥突然微微用力地咬了咬,章决吃了一惊,弓起腿,想用手肘把自己支起来,却被陈泊桥一把压了下去。
陈泊桥抬眼看着他,眼神很静,如同在征询章决的意见。章决的脸很快热了起来。
章决没说话,陈泊桥也不再继续,他直起身,坐回沙发上,又拉了拉章决的胳膊,章决意会陈泊桥的意思,跨坐到他的腿上。
“不想做吗,”陈泊桥抬眼看着章决,表情看上去还挺正经的,拇指却捻按章决微微红肿的乳头,好似正认真擦拭他留下的湿痕,“都一年了。”
“想的。”章决说。
他低着头,尝试去找寻陈泊桥的嘴唇,陈泊桥按着他的背,没有保留地接受章决的吻。
陈泊桥确实是很守信的人,章决想,他答应章决不躲,就没有再躲过任何一次,总是对章决的要求照单全收。
按在章决胸口的手往下滑,经过章决的肋骨,肚脐,褪下章决的内裤。
章决坐起来一些,把脸颊贴在陈泊桥的颈间,腿根着打颤,情动的体液往下淌,陈泊桥的手指从他的大腿中间往上,抹走了少许。
下一刻,陈泊桥托着章决的臀,将他抱起来,让他后仰,平躺在沙发上。
陈泊桥自上方看章决,有很短暂的一秒钟,章决想起了他们第一次做爱的情景,因为当时也是这样的体位,而陈泊桥甚至不愿吻他。
但在在含氧量稀薄的森那山顶,比情趣旅馆的电动床跟简陋的沙发上,陈泊桥的眼神变得这么温柔,就算是章决都不会错认,因此在下一秒,章决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陈泊桥撑开章决的身体,缓缓进出。章决由陈泊桥摆弄着,把腿折起来。
也许是怕弄伤章决,或是想循序渐进陈泊桥做得并不算很激烈,只是掰着章决的腿,持续地进出。过了一会儿,章决的生殖腔像是因为尝到过甜头,没有了从前的生涩,自然地向陈泊桥打开了。
陈泊桥好像也有些难以控制,他把章决的腿根抓得很疼,不断顶送,液体从连接的地方被挤出来,房里只有肉体交缠的声音,与章决断续的呻吟。
他们太久没做,章决很快被陈泊桥操得射了,粘稠的精液弄得肚子和肋骨一片狼藉,章决失力地张嘴喘气,又被陈泊桥堵上了唇舌。
射在生殖腔里的成结带给章决缓慢的胀痛,章决小腹紧抽着,狭小的生殖腔被捅捣得松软,装满了精液,看着自己的下腹被顶起不明显的曲弧。
章决看了一眼,移开了目光,但陈泊桥还是看着,还伸手罩住了,轻按了按,章决让他按得四肢发酸,忍不住叫了一声,又很轻地叫陈泊桥名字,陈泊桥才停了手。
章决闭着眼,感到陈泊桥啄吻自己的后颈,而后渐渐下移,来到已经平整的伤口。
又过了少时,有牙齿磕碰到了章决腺体外的那层白得近乎透明的皮肤,海盐与松香混进了苦杏的气味之中。
陈泊桥的标记像一种拥有理性的兽欲,一场漫无边际的山火,将章决短梦里留下的失落和无望烧灼了起来,浓烈的烟雾蔓延着,蒙上眼睛,扼紧咽喉。
章决将自己彻底地、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再在陈泊桥的吻、性和爱中重得氧气。